
作为一项保障民主、维护人民、加强权力制约的复杂工程,问责制拥有着特殊的文化背景,体现一定的文化内涵,反映文化的发展水平。政治文化积淀的不同会导致问责作用力的不同,即其作用的大小取决于公民的民主观念、法律素质和监督能力。全体公民必须在“自觉的认识”下才有“自觉的行动”。而必要政治文化土壤的缺乏,则会导致大众的误判和官员行为的偏失。因此,问责制的良性运行,并充分发挥监督和警示作用,归根到底是一种文化积累和释放的过程,它不仅要通过法律制度来保证,更重要的还要靠社会的政治文化底蕴来实现。具体说来,政治文化的构建对问责制度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政治文化有助于重建从政道德,强化官员的自律意识。负责任是现代民主政府应具备的基本品质,是现代民主社会与传统专制社会的最大区别。无论是西方议会制还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都是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的实质是一种委托关系,即公众委托其选出的代表或议员行使权力。因此,尽管中西方对民主的解释不尽相同甚至差别显著,但都把责任作为民主政府的一个基本内容或本质特征。但在我国这个有着二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家里,“官本位”的观念根深蒂固。传统行政观念表现为“权力至上”,主张权力的随心所欲、放任自由,而在责任信念、责任评价等方面则表现出冷漠无视的态度。与传统的官场文化相比,新的政治文化的核心是破除“官本位”思想,建立“以民为本”的新从政道德,其目标是树立权责一致的理念,打破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的“位高权重责任轻”的官场潜规则,使官员们意识到:为官从政越来越成为一种权力与责任并存的职业,必须从以往的“我当多大官就有多大权”转到“我当多大官就有多大责任”上来。如果他们已经将一套职业道德观深深内化在心中,形成了某种坚定的道德责任信念,即使上级不在场或面临外界某些诱惑,官员的内心自我控制仍发挥作用。当某些行为缺乏相应法律规定时,官员仍可求助于内心的道德指导准则,进而作出合乎公共利益的选择。
第二,政治文化有助于培育现代公民意识,造就主动问责、高度警觉的公民社会。古今中外,对公权力有截然不同的认识。在西方,人民思想得到普遍认同,并融化于公众与公权力的交往与评判之中。“政府是纳税人供养的,理所当然应为纳税人服务”这一理念在西方得到普遍认同。而在我国,民众对政府的期待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烙印非常深刻,民众对“清官”的依赖心理、官员为民“作主”的意识至今还被广泛认同。这与西方国家公民对公权力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别。虽然中国目前已经进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阶段,但至今依然保留着与传统社会有着天然联系的“臣民意识”,缺乏与现代民主社会相适应的“公民意识”。中国老百姓的“善良忍耐”,成就了一些官僚骄横跋扈的观念。新的政治文化不相信任何身份、等级和特权,强调公民应该具有独立自主的人格和尊严,强调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这正是“公民意识”的本质所在。“公民意识”的确立和普及,将造就一个强大、活跃、警觉的公民社会。官员的“好”或“坏”、“去”或“留”让民意作主,是公民社会的一种常态。以参与政治和制约国家权力为使命的公民社会兴起,为公众问责政府行为的实施和政治民主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它将分散的个人资源和能量聚集在一起,把个人拥有的自然权利汇集成公共权力,使民间的零散呼声转变为团体的诉求,从而对政府及其官员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为现代民主社会建设奠定重要的结构基础。
第三,政治文化有助于发挥补位功能,弥补刚性问责制度的“盲区”。作为法律都具有明确、规范和强制力保证的显著特点,它是刚性规范。但是法律也有其固有的弱点,因为无论是世界上哪一国家,即使是世界上法律最完备的国家,法律也不可能涉及到所有领域中所有事项、所有细节。表现在繁杂的公共事务面前,法律制度有时显得软弱无力。例如,一个官员的行为有过失或不当,特别是违反了道义责任,即明显违背了社会公德和良俗,但是如果没有触犯法律,也没有违纪政纪,那么,仅仅依靠法律等刚性机制就往往难以追究其责任。法律对于道义责任追究的无力,无疑为政治文化这一柔性机制的补位功能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柔性机制与刚性机制往往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在西方国家,官员引咎辞职往往不仅是基于具体的、成文的刚性制度规定,更是基于其深厚的、积淀多年的问责文化及其随之而来的舆论压力。2004年4月17日世界许多媒体都不约而同地报道了德国央行行长恩斯特•韦尔特克因免费住酒店而不得已引咎辞职的消息。德国央行行长免费住酒店当然是“小事”,而且也没有明文规定他必须因此而辞职,但是德意志联邦银行执行委员会却说:“他的引咎辞职从维护银行的声誉和任务来看非常恰当”。这正是政治文化对于刚性问责制度补位功能的具体体现。
由此看来,在公共行政中,政治文化是推行行政问责制的重要外部条件,而培育和提升政治文化应通过以下两个根本途径有机结合来实现:
一是通过教育,把与问责制有关的特定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传输给官员和民众,并通过社会舆论等对其行为予以导向和制约。在人们的观念和印象中,只有东方国家是讲求道德约束的,西方国家的法治传统向来忽视道德的力量,这其实是一种误解。西方国家非常注重加强国家公务员的职业伦理教育。他们的经验是,控制国家官员越轨的重要手段,并非制定越来越多的规则及严酷地进行处罚,而是提高官员们的法律意识、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近年来,西方国家颇有远见地注意了这方面的教育。通过舆论宣传、职业培训、定期考核等一系列的活动,使他们更巧妙地运用了道德伦理的力量,作为民主、正义、法治的坚强盾牌,抵制腐败对于公务人员的感染和诱惑。在行政管理和官吏选任中,西方世界也重视道德的力量,他们对于国家官员的道德要求和道德约束十分严格,甚至近乎苛刻。这也是应该令有着悠久的文化和道德传统的中国深深思考并加以借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也的确富含着“道德从政”的经验,如以民为本、立身为正、廉洁奉公、见利思义、循法守礼等道德观念,都应在现代社会中得到表现和弘扬,形成道德谴责的强大力量,使国家公职人员识别自己行为的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建立公权力行使的内在的自我控制的心理防线。
二是通过道德性的立法,建立制度性的道德准则,以外部控制制度的形式实现官员责任行为或道德自觉。在此,制度性的道德准则既是从政道德化的内容和要求,也是实现官员道德化的途径。事实上,当今世界行政发展的明显趋势是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相结合,重视道德建设的制度化,其重要手段是进行道德立法和建立专门的行政道德监督管理机构,并进而追究政府及其行政人员的道德责任。早在1978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政府道德法案》。1993年,美国又颁布了《美国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加拿大、墨西哥于1994年分别颁布了《加拿大公务员利益冲突与离职后行为法》、《公务员职责法》。英法德荷等发达国家都先后颁行了类似的道德法典。在亚洲,韩国于1981年颁布了《韩国公职人员道德法》。日本于1999年颁布了《国家公务员道德法》。同时,根据法律还建立专门的行政道德监督管理机构。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英国的公共生活准则委员会和加拿大的政府道德咨询办公室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这些机构,或为实质性权威机构,或为咨询性机构,或隶属于行政权力,或隶属于立法或司法权力,甚或享有自主性的权力,它们都在追究官员违反道德行为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文章为用户上传,仅供非商业浏览。发布者:Lomu,转转请注明出处: https://www.daogebangong.com/fr/articles/detail/pvyei6006g60.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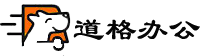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196条)
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