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会想当然地认为“文”、“字”同义,“文”也是“字”,“文字”是个重叠词,就是“字”。实际上历史地看,“文”和“字”是两个东西,两回事。
概而言之,“字”是有声之“文”,而在“字”之前,“文”早已存在,但却是无声之文。“字”是在“文”的基础上发展而出,“孳乳”而出,无声之文,和声相结合,就产生了字。
“字”的本义与“文字”无关,而是和婚育生子有关。其字形为,上“宀”,下“子”, “宀”代表房子、家,“子”为孩子。字形含义为在家中生养孩子,与“文字”之“字”没有直接关系。用“字”来指代“文字”之“字”的唯一原因是,强调“文字”之“字”是被生养的孩子。“字”是被谁生养的,谁是“字”之母。答案是“文”,是“文”“孳乳”了字,“文”乃“字”之母,“字”乃“文”之“子”。
这意味着汉字的出现并非一个从无到有的突然过程,而只是从“文”到“字”的孕育和演变。甲骨文只是“字”的初始形态和起点,并非是“文”的。在甲骨文之前,中国早已存在成熟的“文”系统,而且这个“文”系统又有两个子系统:易经八卦符号系统,和契约符号系,但主体是契约符号系统。
所谓的契约符号系统,就是结绳符号系统和书契符号系统。结绳和书契是汉字开始普及应用之前,契约的两种形态,也是契约的最原始形态。汉字开始普及应有后,契约的形态开始文本化,结绳和书契被文本化的契约所替代,开始迅速边缘化,甚至消失。结绳消失了,书契则被边缘化。这个过程发生在战国时期。期间,书契也被进行了文本化改造,即在书契上写字,记录更多的信息。当纸被发明以后,文本化契约开始成为占据绝对主流。
甲骨文是在以契约符号为主体的“文”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契约符号是甲骨文的字形结构的基本来源。即甲骨文的构形基础是对契约符号的借用,包括结绳符号和书契符号,而非是对具体事物的直接象形。因此,从根本上来说,甲骨文是“契约文字”,而非“象形文字”。也可以这么说,甲骨文是是继承的,而非白手起家的,是二手的,而非原创的。
关于“文”与“字”的区别,以及由“文”到“字”的演变,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进行了记录: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这段话是对汉字起源史的系统梳理,也是最早的,非常重要。许慎明确地将汉字与易经八卦、结绳和书契联系起源,认为这三者都是汉字的前身,这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许慎没有能够正确指出八卦、结绳、书契的属性,及其与汉字的区别,即未能区分“文”和“字”,从而也没有弄明白“文”和“字”的演变过程。在对八卦到汉字的演变过程的具体描写上,基本是臆断。他直接将“书契”等同于字,同时又错误地将汉字的产生说成是“象形”。
但是,许慎却清晰地记录了“文”和“字”的母子关系:“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许慎将“书写”的源头追溯到“书契”是正确的,将“书契”说成是“文”也是正确的。同时,许慎把“书契”之“文”看成是“字”的基础,并进一步指出,“字”是由加上“声”而孕育的,也是正确的。许慎唯一的错误是,混淆“书契”和“字”,混淆“文”和“字”却是错误的。许慎实际上把“书契”、“文”看成是一种基础字。
其实“书契”是契约、契约符号,是“文”而非“字”。同时书契的出现时间也远早于黄帝时代,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契齿文来自半坡遗址,可以上溯到7500多年前,比黄帝时代要早3000年左右。
许慎尤其提到“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这个“形”其实就是“文”, “形声相益”就是“文声相益”,因为他前面说了,“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也就是说,许慎基本正确地记录了汉字的起源过程:文和声的结合。
“声”就是语言,与“声”相结合,就是与语言相结合,并用来表达语言。而“字”之前的“文”则是完全则是无声的,没有发音,完全与语言无关的独立的符号系统。
这就涉及到汉字与其他任何文字的不同之处,包括所谓的古两河文字和古埃及文字。中国在汉字出现之前,就存在一个历史悠久的独立的“文系统”,汉字正是由“文”所孕育,因而具备了强烈的“文”的特征。因而中国的字被称为“文字”。而中国之外,其他任何文明、任何地区,在字出现之前,都不存在独立的文系统,他们都是有“字”而无“文”,他们的“字”是没有资格称为“文字”的。
“字”仅仅是语言的符号化,语言的工具,完全依附于语言,而“文字”的字形中则具备独立的意义,“文字”具备相对的独立性,并不是单纯的语言的符号化,语言的工具,并不屈从于语言。
再次强调一遍,只有汉字有“文”有“字”,有资格称为“文字”,其他任何的字,都没有资格称为“文字”,而因为他们的文化和历史中都是没有“文”的,仅仅出现了“字”,这些“字”中也是没有“文”的特征。
同时,“文”与“声”、语言的结合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非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中,“文”与语言结合的紧密程度、文与语言的同步性在渐次加深。根据与语言的同步性程度,汉字的发展可以区分为三大阶段:甲骨金文阶段、文言文阶段、白话文阶段。
甲骨金文阶段即商朝甲骨文和西周金文阶段。这个时期,汉字还处于初始阶段,与语言的结合程度还非常低,与语言的同步性还非常差,对语言的表达能力还非常低。对甲骨文金文来说,“文”的特征大于“字”的特征,是“文”而非“字”。同时,这个时候,汉字并没有在日常生活使用,而仅仅用于祭祀,甲骨文材料和金文材料实质上都是祭品,是献给神的,给神看的,而非是给人看的。因此可读性非常差,所谓的佶屈聱牙。
在日常生活中,此时还是相当于没有文字,结绳和书契依然流行,是契约的两种形态。社会的秩序也主要靠契约来维持,而非政府。其实,政府本身也是高度契约化的,其政令系统就是一个改造的书契系统。
值得指出的是,在《五经》中,《尚书》、《易经》、《春秋》经文的文风与甲骨文金文高度一致,可以认为这些经文的成书是在西周时期。《春秋》经的成文在春秋时期,但是其格式显然在西周成熟。
“文言文”的出现是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尤其是在战国时期。顾名思义,“文言文”就是“文与言”结合的文,或者用“文”来表达语言的“文”。“文言文”的出现事实上是整个社会“礼崩乐坏”在文字上的表现,也是一个汉字的重大变革、革命,是文字领域里的“礼崩乐坏”。
“文言文”是出现是汉字的一场革命,其实,到了“文言文”阶段,汉字才是真正的“字”,“字”的特征才大于“文”的特征。对甲骨文金文而言,则是“文”的特征大于“字”的特征。因为,只有到了“文言文”阶段,汉字与语言的结合才足够紧密,才能够被用来表达语言。即便如此,文言文还是与语言保持着距离,并不完全同步。因此,文言文还保持着相当程度的“文”的特征。直至2000多年后的另一场文字革命,汉字才彻底语言化,彻底沦为“字”,“文”的特征彻底消失。就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汉字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白话文阶段。
由于只有中国在字之前存在独立而成熟的“文系统”,也只有在中国,字的出现是一个“文”与语言(声)逐渐结合的渐变过程,其他任何文明和地区由于没有独立的文系统,字的出现就是一个直接表达语言(声)的过程,就不存在“文”语言的逐渐结合的过程。
甲骨文金文以及文言文,都是汉字发展过程中因“文”“声”结合的不同,而呈现出的阶段和形态。在这个两个汉字的形态和阶段中,汉字都具备“文”的特征,从而与语言并不同步。对汉字之外的其他任何字而言,都不存在这样的形态,他们只有一种形态,就是白话文。
现代的欧美人捣鼓出来的所谓的文字学,想当然地把文字看成语言的符号化,看成语言的工具,把这一点当成一个文字学的基本前提,基本假设。这对汉字之外的字是成立的,但是对汉字却不成立。
对于汉字而言,字是“文”与语言相结合后的产物,即许慎所说的:“形(文)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由文)孳乳而浸多也”。这一过程,恰恰被两个甲骨文字形记录下来,就是“尹”和“史”。

“尹”的甲骨字形为手持竖直的细棍。王国维等人将“尹”字中手所持的细棍解读成笔,”“尹”为手握笔形。做出和接受这一解释也不困难,因为”笔”字本身也是从”尹”字派生。”笔”的本字为”聿”,甲骨文时期“笔”、“聿”同字,或者说,“笔”是“聿”的一个义项。战国时期,“笔”由“聿”加“⺮”而从“聿”中分化独立出来。
而甲骨文“史”与“尹”有两点不同。一是,在“史”中,“笔”高举在上的;二是,“史”中的笔上多了一个“口”。
在甲骨字形中,手,尤其双手高举的动作是代表敬神,对神的崇敬。譬如甲骨文“典”的字形为双手举着“册”。“册”就是“甲骨册”,即穿成串的甲骨片。“典”就是将“册”作为祭品献给神的祭祀仪式、场景。
“史”将笔高举在上,就是在表明,“史”所书写、刻写的内容是用于敬神的。实际上,“史”用笔所刻写的正是甲骨文,而甲骨的用途就是穿成串成为“册”,而用于祭祀。
“史”中笔上的“口”,指的是语言,意思是说,“史”所刻写的是与语言相结合的“字”。“尹”中笔是在手的下边的,没有高举的动作,而且笔上也没有“口”,这意味着“尹”刻写的内容不是敬神的,同时,所刻写的内容也与语言无关,是一种“字”之前的“文”。
具体来说,“尹”正是在书契中作为契约中保的“大人”,他们不仅负责“评理”,已达成共识,而且帮助契约双方刻写书契。因此,“尹”中的笔实际是刻写书契的刻刀,所刻写的是代表数字的契齿文。而契齿文是“文”而非“字”,完全与语言无关,没有发音。
“笔”、“书写”都是起源于书契,“尹”正是最早持笔书写的人。不过“尹”的书写方式是刻、刺,而书写的内容则是契齿文。
从“尹”到“史”的变化正是从“文”到“字”的演变,“史”也是书写者,书写方式也是刻、刺,但是书写的内容却已经是与语言(口)结合的字了。“史”是中国历史上首批书汉字书写者。
文章为用户上传,仅供非商业浏览。发布者:Lomu,转转请注明出处: https://www.daogebangong.com/articles/detail/The%20appearance%20of%20Chinese%20characters%20is%20a%20gradual%20change%20from%20wen%20to%20character%20evidence%20from%20oracle%20bone%20inscriptions.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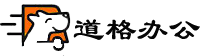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196条)
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