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兆言的《陈旧人物》近日又出增订本,内容更为充实,收录了作者十余年间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著名文化人物的散记,所记叙的人物涉及国学、文学、史学、书画各界,上至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下至苏青、张爱玲等江南才女,既有林琴南、闻一多、朱自清、吕叔湘等文学大家,又有齐白石、张大千等画坛巨匠,还有笔者感到生疏的范烟桥、蒋百里、王泗原等。而这些让人高山仰止的历史人物,在作者笔下变得亲切随和,一个个走下“神坛”,多了点世俗气,带了些人情味。
写到康有为,作者戏谑地说他“爱吹牛”,对这位“康圣人”天真的“大同理想”的想法更是持怀疑态度,正是作者的诙谐,一下子让这位大名鼎鼎的康圣人变成了一位极具人情味的老头子,着实可爱。
谈到林琴南,人们记住他是因为他的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曾“一时洛阳纸贵”,累计印量达十万册,风靡了一大群痴情怨女,成为当时红极一时的超级畅销书。而作者认为这正是林琴南的悲哀,因为林琴南本人并不推崇自己的翻译,而且由翻译带来的巨额稿酬更是林羞于启齿的难言之隐;而林最为看重的“古文译法”,却让自己背负上了“桐城余孽”的臭名,在长达近一个世纪中,成为历史上的“反面”人物。叶兆言为其“古文译法”正名,不能不说其眼光独到。
文学家写历史人物,自然少不了文人的奇闻趣事,叶兆言更是自然坦率,正如他在文中所说,“一个作家最大的幸福,是一吐为快,把内心深处想写的东西写出来。” 比如写很多人物的脾气秉性,作者如数家珍。就拿顾颉刚来说,其性耿直,口无遮拦,曾因得罪鲁迅,而屡遭痛斥与挖苦,就因为二人脾气都大,所以之间的隔阂始终没有解除。而俞平伯,在作者的印象中则是个老小孩,不仅少爷脾气,还爱卖弄才气。写吴宓,则写尽了其“风流韵事”,其感情丰富,一生爱过的女人无数,而且时常请女学生吃饭,荒唐时,竟然还为女学生作弊,自己翻译的文章,署上女学生的名字,推荐去发表。当然这些都是发乎情,止乎礼,毕竟他的一言一行,都是以圣人为榜样,绅士般地尊重女性,于今日之“玩弄女学生”不可同日而语。大画家齐白石因为生活的贫穷而抠门到不行,即使在有钱的时候,过的也是穷人的日子。据说齐家总是用一个木箱子盛米,木箱子上面还要加一把锁,钥匙由齐白石掌管,他的儿媳妇每天做饭,都要去请他开锁,齐白石怕媳妇浪费,每顿饭都限定四小铁罐,天天如此,除非这一天来了客人。
文学世家出身,叶兆言也比平常人多了接触了解名人的机会,或者亲眼所见,或是从祖父叶圣陶先生及其好友那里道听途说,从活生生的日常生活的细节出发,把众多人物的形象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写俞平伯,这位作者印象中的“老小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西单附近的一家烤鸭店里,穿着旧衣服,津津有味地吃烤鸭,看上去像个淘气的老和尚。作者正好与姑姑、大伯母也去此店用餐,所以描写当时俞先生吃烤鸭与穿着寒酸的情景真实动人。朱自清是出了名的没有架子的人,作者听吴组缃说过一件事,话说一位学生打电话到朱自清家,说有几本要看的书找不到,让朱自清速去图书馆帮着找一找,时值清华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竟然被学生差遣犹如使唤老妈子,还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写郑振铎与王伯祥,作者用祖父的观察将二人在逛书店时的表现作对比:郑振铎进了书店,立刻丢魂失魄,把带去的朋友忘得一干二净;王伯祥进书店就要发牢骚,红着脸说“根本就没有书”。郑是到处有书,王是只知道找他需要的书……
读《陈旧人物》,就像跟随作者做穿越之旅,让你不知不觉中走近历史的现场,去看看那些陈旧人物的日常生活,当那些让人学贯中西、通今博古的“大”人物突然不再高高端着身价却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你面前时,你又怎会不被打动?
附:《陈旧人物》节选赏析
顾颉刚
有一次,从王伯祥家出来,时间尚早,祖父说我们今天去看顾颉刚,不记得是没找着地方,还是找着地方人又不在,反正转了一大圈,乘兴而去,败兴而归。我时常听祖父说起这位老友,印象中,他是个对许多事都有浓烈兴趣的人,喜欢收藏,喜欢民歌和民谣,喜欢看戏的戏票和说明书,只要是个玩意,到他手上就是个宝贝。
一九五四年夏天,顾颉刚上调北京,在他老人家的亲自过问下,主持整理《资治通鉴》。当时的北京副市长吴晗不敢怠慢,安排在画舫斋,那是北海附近,庭院内是一株唐朝的古槐,还有几株海棠。庭院东面就是“得性轩”,是光绪皇帝的避暑之地。顾颉刚虽为名教授,安排在这样优雅的环境里,一方面感到极大幸福,“所谓久溷尘嚣,今乃得斯静境”,终于能够安心做学问;另一方面,又不无担心,因为他觉得自己“不死于战乱,不死于谗构,又不死于忧伤”,这番破格重用,难免“声名太盛”,于是产生了“其将雪我耻耶”,“抑将速我谤耶”的疑问。
这种清醒真是难能可贵。顾颉刚是个地道的书生,曾因得罪鲁迅先生,屡遭痛斥和挖苦。鲁迅有脾气,顾颉刚也有脾气,大家都倔,顾后来虽然赠书给对方,但是两人之间的隔阂,始终未能解除。顾颉刚显然不止一次吃过口无遮拦的亏,他在苏州中学演讲,自己作为苏州人,不拍同乡马屁,却大说苏州人的种种不是。他说 “江南人本来很富于创造力,文学尤其发达。可是现在呢?在新文学家中,除叶圣陶外,竟找不出第二人来”。他又说“外面的人都知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看苏州人在天堂中,难道这样的病态之中可以算作天堂吗?唉,老实说来,岂但不是天堂,简直是地狱”。
在五十年代,顾颉刚有着非常好的读书环境,查找资料方便,助手众多,然而来自意识形态的干扰,往往让人手足无措。他不至于像陈寅恪先生那样,公开叫板不学马列,私下里也没少嘀咕。在《缓斋杂记(六)》序中,白纸黑字地这么写着:
马、恩治学基于西方历史,其探索学理则本于固有之辩证法而益加精进,欲治其学,必穷其源,此非有张骞之凿空精神不可。使予再稚三十年者,诚有勇气作此尝试。今则衰老相乘,旧业且荒,而欲广拓园地,非梦想而何!寿丘余子学步邯郸,失其故步,予亦惧夫蹈此覆辙以为世笑也。第今日之局,只许进,不许退,则予虽欲 自守而势有不可。无已,惟有藉病屏却人事,俾得一意读书。有成则自喜,无成则其命也。
邯郸学步是五十年代的人文景观,一代知识分子失去根本,从此找不到北。有太多例子可以举出来,作家应景修改旧作,学者忙着订正观点,在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不仅屡见不鲜,而且一度非常时髦。顾颉刚敢称病顽抗,已属十分难得,反对他的人,只要抖出与鲁迅争论的旧案,就足够他吃不了兜着走。后人不熟悉当时的残酷气氛,误以为顾颉刚钦命在身,有尚方宝剑护着,谁也不敢把他怎么样,其实历史罪行和现实表现两者一结合,随时随地可以置顾颉刚于死地。历史早已证明,一九五七年打“”,很多人榜上有名,是毫无道理,很多人当时没有被打成“”,同样毫无道理。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在那种极端的岁月里,没什么逻辑可言。
我祖父最看重的朋友,不是写小说的作家,而是能有耐性做学问的学者。早在八九岁读私塾的时候,祖父就与顾颉刚认识,可惜先生管教太严,两个孩子竟然没说过几句话。 顾颉刚年轻时一度迷恋政治,“慷慨好任事”。他参加了中国社会党,很快就成为党的“中坚分子”,“而圣陶、伯祥觉党中人物气味不投,相率避去,虽开大会亦不到矣”,他因此“愤诃之,一时有交恶之状”。顾颉刚在思想上显然要比祖父和王伯祥激进许多,当时他新婚不久,初为人父,在上海神州大学读书,为了革命理想,竟不惜别雏抛妻,不惜中断学业,远赴北京,做社会党的党务工作。可惜“职业革命家”的身份,毕竟不对他的胃口,他很快目睹了政治的种种黑暗,所谓 “藏垢纳污,集卑泄鄙”,于是“清夜以思,悲从中起”,于是发誓“他日入校,定习农科”,并且要“终老于此”。
顾颉刚一九一三年春季考上北京大学,是读哲学,还是中文,我始终没有弄明白。他毕业的时候,已经是五四以后,为什么要读那么多年,也仍然不清楚。我只知道,他的思想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完全一致,如果说在后来,顾颉刚还保持着什么政治理想,那就是当时流行的科学和民主。他以毕生的精力研究国学,无怨无悔,可以说自从进了北大校门,人生目标就此锁定,再也没改变过。
文章為用戶上傳,僅供非商業瀏覽。發布者:Lomu,轉轉請註明出處: https://www.daogebangong.com/zh-Hant/articles/detail/pxms3g00i8zg.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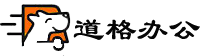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196条)
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