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葛剑雄,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原所长,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博导,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本刊编委。
《同舟共进》:可否请您谈谈所学过的历史课本,它们对您的学术研究产生了什么影响?
葛剑雄: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无论普通民众还是高层领导而言,他们获得历史常识最基本甚至是唯一的来源,就是教科书。因此我们有很多错误和片面的概念,甚至在学术界也很难消除。其实我本人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念小学时看过一本通俗的历史读物,大概是《中国历史故事》一类,我的很多历史概念都是从那里来的,跟课本所教没什么两样,不过是详细一点。至于现在的历史概念,那还是在“”结束,自己从事专业研究,在看到一些境外的有关中国的历史著作,对一些习以为常的概念产生怀疑后形成的。这也得益于我的研究生导师谭其骧教授,他当时在主持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主张历史考证要实事求是。举个例子,过去的历史教科书都强调早在三国时期孙权就派卫温、诸葛直到了台湾,以此证明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却从未讲到卫温、诸葛直去的目的是什么。老师让我们查阅史料,一看才知道他们是去掳掠人口的。书本以此证明大陆跟台湾从那时起就是友好往来,这一方面是歪曲历史,另外对促进两岸统一也没好处。1986年我参加了美国的亚洲学会年会,会上一些台湾的学者跟大陆学者发生了争执,台湾学者质问:如果这是中国的土地,为何还派人去掳掠人口?当时的大陆学者一脸茫然。所以某些我们自以为正确的概念,有时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当然,任何国家的教科书跟学术研究还是有别,它体现的是国家意志,为了符合主流的意识,也都会有所选择、有详有略,但这里有个前提,即不能歪曲事实,不能片面地戏说历史,这是教科书的“底线”。
《同舟共进》:您对当下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有何看法?
葛剑雄:前些年我参加过历史教材的评审和历史课程标准的评定,对教科书的情况有所了解。这些年,我们国家的教材已不再是全国统一的了,现在教材编写的流程大致是先由教育部管教材的机构成立一个委员会,负责制订课程标准,以此作为编教材的根据。然后由各出版社编写教材,完了再送审,审查通过后,这版教材就可以使用了。学校采用哪一种教材是可以自由选择的。现在的教材怎么编,关键要看两个环节,一是课程标准,课标里没涉及的内容很难进入教材;二是教材的评审。为什么现在的教材,大家还认为有些地方不符合事实呢?我想这显然是受政治的影响。
先不谈近现代史,我们的古代史就存在不符合历史事实或观念不正确的情况。原因何在?我想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一是我们的历史研究比较滞后,研究的选题长期以来习惯回避一些所谓有争议的、敏感的问题。比如明朝的倭寇,一般认为倭寇就是日本人,就是海盗,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早期的倭寇基本是日本海盗,但后期就已经以中国人为主了,是中国的武装走私集团对抗自己的政府,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倭寇和日本人画上等号,或都说成是日本人对中国进行侵略。另外,我们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不够,在这种情况下,教材要作出相应的改变就比较困难。比如抗美援朝,尽管现在很多史料都已披露,但这方面的研究还是经常会遇到阻力,包括许多材料也还是“内部”的,若要在这时修正教材的说法,往往编者本身跟评审人之间就没办法统一。再者是我们历史学界某些权威学者的观念还比较保守,思想较为僵化,尽管有时并没有官方的指示,甚至教材也已作出某种程度的改变,他们依然持否定态度,依然坚持旧说。
《同舟共进》:以人教版历史教材为例,初中阶段普遍采用编年体方式编排,高中阶段又将编年体方式打乱,采用政治、经济、文化几大模块的组合,您怎样看这种编排方式?
葛剑雄:我们的历史教育在不同阶段主要达到什么目的,整体的目标是什么,尚不明确。所以容易给社会各界造成一种误解:历史就是背年代。别人听说你是学历史的,就会说你的记性很好啊,这么多的年代和人名、地名都背得出来。像中国史和世界史,我们一直都是分开教学的,以致现在很多人包括一些专家学者或高层人士,缺少一种“世界中的中国”的概念。我们一直认为中国历史悠久,这当然是相对于历史只有两百多年的美国而言,如果跟世界的文明古国相比较,中国算得上历史悠久吗?又比如我们讲中国的文字如何了得,但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距今也才三千多年,我们可以看看楔形文字、泥版文字多少年了。这种概念为什么没有呢?一方面我们总爱有意无意突出这一点,另外我们从没把中国史和世界史结合起来,没有比较的眼光。我到台湾的故宫博物院参观时,看到里面的大事年表在走廊里一字排开,都是将中国史和世界史并列在一起的。到了近代历史,我们开始作中外比较了,而往往又存在片面性。我们的教育到底要给学生树立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观念?如果是树立一种正确的史观的话(这当然跟哲学不同,它不是抽象而是具体的),很多历史事实只需点一下就可以了,到了后期便可放手让感兴趣的学生自己去看书、学习,否则你整天讲故事都讲不完。
《同舟共进》:就您所接触的大学教育情况看,会否碰到一些学生,在中学阶段固化下来了一些陈腐甚至是错误的历史观念,而到了本科、研究生阶段,要花大量时间进行再教育?
葛剑雄:不要说高校的学生,就是一些学者也持有某种固化的观念。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理论讨论会”的论文集里,历史类的论文有两篇,一篇是我的《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还有一篇是北大罗荣渠教授的,他已经去世了。这两篇文章被选中,都因为它们涉及史观,而非简单的历史事实。我文章的中心是说明中国不能简单地讲“统一的时间越来越长,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支流”等,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观点。总结到今天,就是我们的改革开放要充分发挥中国历史上统一的优势,也要克服长期在专制制度下形成的弊病。同时说明,中国进步的动力并不像历史上那样来自分裂,而是来自改革,若能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职权,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就可以克服历史上不得不通过分裂才能形成的历史的动力。这篇文章在当时是得到肯定的,还获了“论文奖”,但以后就不断有人找麻烦,有的说这是“”,有的说是在鼓吹分裂,甚至说这是为“”张目,等等。这里的情况很复杂,有些人不一定主观上就坚持错的,这是他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概念,已经固化下来,是动不得的。
再举一个例子,比如郑和下西洋。历史课本的解释是片面的,说郑和下西洋是促进各国人民友谊,是和平的使者等。真实的情况根本不是这样。实际上,在郑和的时代,明朝统治者认为自己就是天下的中心,周边的蛮荒小国都必须服从我,我天朝大国有的是财富,我来是给你们赏赐的——当然这跟殖民主义有区别,但没有建立殖民地并不代表他尊重外国。如今却片面解释这段历史,好像郑和下西洋完全符合现代政治文明,而且我们研究郑和的学者居然也大多持这样的看法。这本质上不是教材的落后,而是我们学术研究的落后,观念的保守甚至已到了顽固的地步。这对学生造成的影响,是要持续到下一代甚至下面几代的。
《同舟共进》:目前情况下,要教材作出改变其实是困难的事情。
葛剑雄:2007年上海推出新版高中历史教材曾引起争议,我认为上海的教材尽管有缺点,但它是一个很可贵的探索。当时的美国媒体称“用盖茨替代”等报道是片面的,这个片面的报道被一些人作为理由,给上海方面施加压力,甚至扣上反动、颠覆等帽子,虽然没有强令禁止,但最后这一版教科书还是停用了。这是很可惜的。
《同舟共进》:上海版教材的可贵之处在哪里,现在的教材存在哪些问题?
葛剑雄:那就是它比较全面地解释了历史,基本观点还是有进步的,没有把历史仅仅看成是政治或阶级斗争,另外,编排的文字也不错,应该说更受学生的欢迎。有人用“教材编辑的时间太仓促”作为停用理由,这个很可笑。大家要的是结果,如果不完善可以继续修订,编两三个月和编一个月又有什么关系呢?反过来看,我们有些编写得更仓促的读物都在用,这又作何解释?
现在看来,我们的教材普遍缺少一种人文观念和价值观念,这才是大问题。比如我在审查教材时,看到二战胜利的部分,上面写道“日本政府的代表某某瘸着一条腿踏上密苏里号”,我就提出意见:应将这段话删掉,因为这是人身侮辱。日本代表(重光葵)的腿尽管是被韩国志士炸伤的,是侵略者罪有应得,但我们不应该在残疾这一点上对他进行丑化,而且作为日本政府代表,当时的盟军也还是给予他礼遇的,这是一种国际惯例。后来编写者接受了我的提议。有一次,我在日本联合国大学作报告,下面有日本听众提问:你们指责我们的教材有问题,那你们的教材有没有问题呢?我回答,任何一个国家的教材都可能有不妥当的地方,我们发现的话也会修改的,我就举了上述这个例子。
还有教材里说李鸿章贪污,我也提出这个要有事实根据。李鸿章当时搞洋务运动,他的家世确实很富裕,族中兄弟也有很多当官的,但他具体拿了哪一笔钱?曾国藩的弟弟是有名的贪官,但曾国藩本身还是廉洁的,所以我们不能笼统地说,凡是搞洋务的人都贪污。又比如我们从小接受的“四大家族”的概念,当时教材有一句话(记不得是政治教材还是历史教材),大意是四大家族的钱加起来,就可以实现中国的农业现代化。现在我们已看得很清楚,孔家是贪污的,但你没有充分理由说蒋家和陈家也是贪污的,相反蒋家和陈家几乎谈不上是有钱人。这样的概念灌输,完全是不顾历史事实的政治化,是不负责任的。
《同舟共进》:您认为,历史教科书未来的改革应朝哪个方向走?
葛剑雄:我主张学历史之初,要教会学生最基本的历史概念和重要的历史事实,而到了后期,就要注意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念,教会他们进一步学习的方法。有些历史观念不一定通过历史课来实施,可以通过比如义务教育阶段的尝试,通过低年级的启蒙等。据我了解,美国的小学一年级是不分科目的,但成绩里面有一门“了解美国的历史”。课本上只是写“美利坚合众国的第16任总统林肯是位好人”,还教他们歌曲《上帝保佑美国》,就是这么简单,没有多少东西。另外,我主张到一定阶段要打通中国史和世界史,不应该完全把两者分开,这样更有利于拓展学生的眼界,有助于他们形成开放的思维。通过教科书让学生掌握独立思考的能力很重要,不单是历史,其他的科目也有这个任务。比如我们的语文,其中有文言文,老师在讲解的同时,还要向学生介绍历史背景,这个历史背景和历史课应该是统一的。如果我们历史的观念已经比较开放,你还在使用那种错误的、保守的观念讲政治,那也是不行的。历史观的教育和基本的历史事实,不仅应体现在历史教材里,还应体现在其他教材当中。
《同舟共进》:最近兴起了一股“民国教科书”热,那时的教科书编写汇集了一批一流的学者,像张元济、叶圣陶、丰子恺等,当代历史研究的学者是否也应担当起这方面的责任?
葛剑雄:民国的一些学者编教科书其实也是为了钱,教科书发行量大,编者是拿版税的,所以当时写一本学术著作可能没有钱或很少钱,但编教科书或许能解决生活困难。我们不要把民国的学者想得那么高尚,任何人都离不开谋生。另外,我们的新式教育是废科举后确立的,当时要兴办大量新式学堂,于是对教科书的需求量猛增。当时的政府对教科书没有统一规定,部分学者就把日本的教材改头换面翻译过来,到后来才有统一的“部颁教材”。我们现在往往将名人编的、好的教材看成是民国教材,其实民国教材不乏粗制滥造,也有很多糟粕。今天我们老提“民国范儿”,这种怀旧流行背后的重要原因就是对当下不满,将一个旧时代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比现在的不好,会给人产生一个错觉:民国就是一个天堂、一片乐土,民国的人都是君子。我觉得这样的评价更多地反映了大家的一种情绪,一种对教条的、僵化的教材的逆反心态。但有一点,民国的教材可以自由地编写、自由地用,当然一些好的教材就可以涌现出来了。要真正评价民国教材,应把民国的所有教材都拿出来,然后再作分析。
另外,社会上并非所有的学者都能编教材,编教材有一定专业性,大学者也许可以给研究生写教材,但不一定编得好中小学教材,现在能编的往往是师范院校的,因为他们有教学研究的背景。我们可以要求大学者写普及读物,但未必就要编教材,这个功能应主要靠社会来完成。我昨天还跟一位记者讲,一流的学者不一定有普及的能力,如果有最好;若是没有,也可以让人家来替他普及。汤因比写了《历史研究》,简写本是人家替他写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提出来后,国际上曾组织过竞赛,看谁有本事用比较通俗的方式将内容介绍给公众。教材也是这样,不一定由一流的学者来编,但编教材的人要注意吸收一流学者最新的成果。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3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文章為用戶上傳,僅供非商業瀏覽。發布者:Lomu,轉轉請註明出處: https://www.daogebangong.com/zh-Hant/articles/detail/pvu1y302caub.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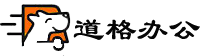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196条)
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