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风口》是近期出现的一部历史意味丰厚、思想意蕴深切、色调悲壮慷慨却又不乏某种喜剧因素的颇为坚实的长篇小说。它写了一页我们永远不该遗忘的历史――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悲壮、曲折、复杂的创业史、奋斗史。自1949年一支其前身为“三五九旅”的解放大军徒步开进新疆之后,大幕随之拉开,在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汉人与少数民族同胞之间,上演了许多匪夷所思的故事,展现出令人动容的苍凉的青春风采。作者自言,这部小说是写给兵团人的,是献给父辈们的,但不也同时是写给今天的青年朋友们的吗?无论对于张者个人的创作,还是对近期的文坛来说,都是一个可喜的收获。
在目前浩如烟海的长篇小说中,《老风口》是创作准备相当充分的一部。作为兵团子弟,张者动用了他少年时代的诸多生活积累,同时他多年来悉心研究兵团史,占有了较为丰富的资料。这些苦功没有白下,作品显得质地结实、内容丰满,是属于有真货的大气势之作。只要看小说从进疆写起,那徒步行走、“人羊大战”、风沙漫天、烈日、闯田、精尻子开荒,直到月亮泉闪亮、金黄羊的显形,粗犷神秘的画面一幅接着一幅,有声有色地展示了艰苦卓绝的创业奇景。与此同时,瑰丽的新疆风光和民族风情场面,也令人沉醉。
然而,它毕竟是小说而不是历史。作品是通过丰富的想象,通过叙述人交叉言说的方式,通过诸多男女主人公的命运来展开宏大生活场景,把这一页历史艺术化、心灵化的。胡连长、马指导、秦安疆、葛大皮鞋、李桂馨、阿依古丽、还有“我”等等人物,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必须看到,解读《老风口》,须从它选择的独特叙述方式入手。它从不同的甚至是有些对立的口吻来叙述同样的事件,向我们展示了历史的多种叙述及其可能性,堪称一次历史记忆的文学的双重想象。它主要由两个不同的声音来讲:一个声音来自马指导员,另一个声音来自“我”――兵团后代、私生子。这两种声音有时是一致的,更大部分则是不一致甚至是相左的。它们的差异构成了奇妙的效果。
张者让这两种声音都用第一人称讲述,每一章的“上部分”大都让马指导员先讲,他是第一批进新疆的兵团人,是26连的指导员,至关重要的是,他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我们是随着一支部队去新疆的,那是一支很著名的部队,抗战时在南泥湾开荒种地出了名,叫‘三五九旅’。”所以,他在讲述自己曾经参与的历史时口气是毋庸置疑的,哪怕讲述的与现实有距离,也不允许别人给他指正。最重要的是,马指导员讲述时的第一人称指示代词不是“我”,而是一个复数的形式“我们”。这是一个颇值得寻味的细微之处。他们当时的进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婚姻,甚至他们的命运都是属于一个集体的,那时没有个体存在的独立性。所以,在马指导员的讲述中,在他的心中,凡事都是“我们”。
比如,“我们”到达新疆后遇到的最大威胁不是土匪,而是饥饿,是物资的匮乏。尽管生活在茫茫戈壁上,大风一年四季在刮,开荒的生活满是艰辛,“我们”依然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和激情。马指导员讲述屯垦戍边的故事,开始的第一句话就是“在那个红柳开花的季节……”,“我们”对红柳的热爱溢于言表。可见他对红柳花印象之深,他讲到所有美好的事情时,都要和红柳花连在一起,以至于把自己的女儿也取名红柳。“马指导员太爱那红柳花了,好像没有红柳花的陪衬,所有的故事都黯然失色。”他把部队进疆的季节也说成夏季――红柳开花的季节,事实则是,进疆时是冬季,这个季节红柳不可能开花。一起进疆的秦安疆是个诗人,他写的诗大都是现代诗,却为红柳写下了一首标准的古体诗。
还一个是异性。“我们”在进疆的路上鞋磨破了,脚也打了水泡,走不动时,“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成了前进的动力,最具鼓动性的口号变成了“打到新疆去,发给你老婆”。胡日鬼和阿依古丽历经磨难的爱情是书中的一个亮点,令人不能释怀的是他们最后寻找阿伊泉的神秘出走。而“我们”在戈壁上第一次见到女兵时热泪盈眶。尽管“我们”当时没有据为己有的意思,想都不敢想;但是“我们”曾经抢过女兵。26连惟一的一个女兵李桂馨是连里谁都爱护的,因为女兵是戈壁上的水。
马指导员一讲完,另一个讲述者“我”就跳出来告诉大家:“也许年代太久远了,马指导员的讲述会有不少漏洞,这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马指导员给我讲述这些故事时已经六十多岁了,他已经退休。当然,这其中有记忆的问题,也有夸张的成分,再加上故事本身又有太多传奇色彩,出现一些差错是难免的。记忆出了问题,我可以给他指出来,一些有意的夸张,一些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我们只能权且听之……” 然而,马指导员向我们道来的,是“我们”自己的故事,在他的声音里,我们和他一起感受上世纪五十年代新疆的戈壁上的一切:春季来临的大风、突然翻浆的土地、瞬间卷走人的狂风、相爱而不能相守的人以及闪现于荒原的土匪……这一切,都是人与自然的博弈、人与人的博弈。
小说的另一种声音的发出者“我”是《老风口》真正的第一人称叙述主人公。细读起来,会发现“我”的叙述竟然又有两重声音。表面上看,“我”的身份是一个生在新疆的建设兵团的后代,是一个兵团史志办的工作人员。为了征集兵团史,我采访了一大批老兵团人,马指导员是其中之一。 “我”的身份既是明确的,又是不确定的。“我”只是把胡日鬼叫爹,但“我”真正的父亲是谁却无从知晓,“我”的娘就是那个26连的第一位女兵李桂馨,“我”能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因为全连没有人愿意担当和李桂馨不清白的罪名,“我”的到来就导致了“我”娘李桂馨的死亡。所以,“我”是一个真正的建设兵团的儿子。作为“我”这一层面的叙述仍然是个人化的叙述,“我”通过自己的记忆展示了一部分建设兵团的历史以及与兵团有关的人和物。“我”出场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当然记得那遥远的胡杨林,因为我就出生在那胡杨林边上的军垦连队里。那个兵团的连队叫26连。”“我”对母亲的惟一记忆就是胡杨:“那棵胡杨树长得确实像一位女人……我没有见过我娘,我心中的对娘的记忆就是那棵树的形象。”实际上,更为隐蔽的也更为重要的是“我”对这段历史的叙述立场,这是“我”的另一层面的叙述,是一种所谓完全遵循历史真实的宏大叙事。如果说马指导员的叙述是夸张的、诗性的、传奇的,那么“我”的这一层叙述则是冷静的、现实的、考证的。“我”肯定了马指导员的叙述激情,“我”大学是学历史的,就是有考证历史的毛病,没办法,这是职业病。对于马指导员所讲的一切,“我”都进行了官方的史实的考证。例如:“马指导员说兵团是在1982年恢复的,其实对于一个基层的兵团人来说,这种说法没有错。不过权威部门把兵团恢复建制的时间认定为1981年12月3日,也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1981〕第45号文件的时间,即作出恢复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的时间为兵团恢复时间。”
《老风口》就是这样,让个人叙述和宏大叙事并行于读者面前,让主旋律的和个人的爱与恨交织在一起,让两种声音自始至终回响于读者耳畔。这部作品有一定复杂性,存在着一系列悖论。比如,固土守边,与恶劣自然环境斗争,是可歌可泣的、英雄主义的;但不大顾及女性的生理特点,要她们干苦活,又是不妥当的。再比如,为征战多年的官兵解决配偶对男方是人道的,但由组织指定,带有一定强迫性,又是非人道的。在这里,既不无专制主义的色彩,同时又是英雄主义的高扬,这里因历史与现实的两种语境,产生了两种价值观的错位,政治话语与人道话语、英雄话语与人性话语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性,于是作品具有了某种深刻的悲剧美。这也许才是《老风口》真正的价值所在。
文章為用戶上傳,僅供非商業瀏覽。發布者:Lomu,轉轉請註明出處: https://www.daogebangong.com/zh-Hant/articles/detail/pukyyp04gq2k.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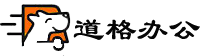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196条)
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