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年上海社科院歷史所召開“八一三淞滬抗戰”討論會,議題是熊月之先生訪德時得到的一批“八一三”照片,熊先生希望我能發個言,我在談完正題後又附帶提到了東京大學藤岡信勝有關日軍暴行照片的所謂“偽造”問題①,表示應該予以重視。我的話還沒說完,一位已退休的先生即刻質疑,認為這些事“我們中國人說了算,不必理會日本人說什麼”。類似的意見在其他場合已有所聞,並不是“偶然”之見,所以我當場也作了答复。大意是:對日本右翼學者的自彈自讚雖不必在意,對問題本身卻不能任其自流;日本右翼學者提出的“偽造”照片的每一張,都有從來歷,內容以至於“釋義”徹底檢討的必要,這不僅是因為有右翼挑戰的“問題”語境,同時也是因為許多照片承自前人,以後的使用基本是“陳陳相因”(我用這個詞時並未含褒貶) ,在時隔數十年後的今天,確應“原始反終”,作一全盤清理。當時談的雖只是照片,其實對文字、實物等其他材料和日本的相關研究尤其是見解相歧的研究,我以為也應如此。南京大屠殺與一般歷史事件的最大不同,用舊話說在於它的“大義名分”,但作為“歷史事件”,我覺得它不應被圖騰化;既然自信它是一個“真實”,從“功利”上考慮,也不必擔憂學術檢驗,無須免檢的豁免權。去年末28卷本的《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出版,南大、南師大等單位聯合舉辦了“南京大屠殺史料國際學術討論會”,會上第一次出現了對一些“定論”的探討,讓人感到這一牽動著學術界以外敏感神經的著名史事“討論已成為可能”②。我一直有一個偏見,以為如果我們更堅持學術標準,更有“彈性”,日本右翼學者的許多觀點本來可以不攻自破,至少不會像現在那麼有市場③。這是我多年來關注日本有關研究的一個突出體會,也是我持續關注日本有關研究的一個重要理由④。
本文所說的“南京大屠殺史料”,取通常的廣泛義。有關這點,先須稍作交代。一、“南京大屠殺”(南京大虐殺)雖一度被日本大屠殺派的主流作為1937年末南京淪陷時所發生的歷史事件的正名,如洞富雄等先生的著作⑤,但在日本不是通稱。東京審判時對這一歷史事件的稱呼是“南京暴虐事件”(日文漢字與中文同,或英譯Nanking Atrocities作“南京アトロツティ一ズ”),今天除了津田道夫,小野賢二等個別學者仍堅持用“南京大屠殺”⑥,大屠殺派的主流漸多以“南京事件”為名⑦;日本虛構派稱“南京大屠殺”時必加引號,以表明是“所謂的”大屠殺,近來更有人對“事件”復加引號,意為當時本來無事,“事件”也是“杜撰”⑧。但大體來說,“南京事件”在日本是一個“約定俗成”。本文所稱“南京大屠殺資料”,即日本所稱“南京事件資料”。這與通常所指其實並無抵觸。二、國內學界雖對南京大屠殺的內涵尤其是諸如人數等的關節點有明確而嚴格的界定,但對材料的取用卻十分“寬大”。有些文獻的確切含義,比如能證明什麼?能證明到什麼程度?通篇的意義如何?摘出的某段與全篇精神是否吻合?材料本身是否可靠?特別是有些口傳記錄的真實性,比如訪談的環境是否有“表達的自由”?採訪者對被訪者是否有“導向”或暗示?被訪者所談是否合於實際?如以歷史學的尺度來衡量,不能說都已得到了嚴格的檢查和令人滿意的解答。之所以同樣的材料會得出不同以至於相反的結論,這是一個重要原因。所以,本文不“以貌取人”,各派所編“南京事件”的主要資料都在論述範圍之內。
本文分上下兩篇,上篇簡介日本有關史料,下篇綜論日本史料的價值。下篇為本文重點。

上 篇
日本對“南京事件”持不同立場的三派(屠殺派、中間派和虛構派)都編有資料集,作為自己一派主張的援據。按形式分,有文獻和口述二大類,按來源分,有日方官私文獻和西文中文文獻的日譯。以下先按屠殺、中間、虛構三派所編順序簡介資料集。
一、屠殺派
1.《南京事件》
洞富雄編,河出書房1973年出版。此書是《日中戰爭史資料》的一種,分Ⅰ、Ⅱ兩卷(《日中戰爭史資料》第8、9卷)⑨。 Ⅰ卷收錄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有關“南京事件”的日文記錄,共分五個部分,即:(1)起訴書,(2)審判速記,(3)未宣讀的法庭證據(檢方書證) ,(4)不提交書證(包括檢、辯雙方),(5)判決。
Ⅰ卷中審判速記的篇幅最大,包括了從1946年7月25日原金陵大學醫院醫生(指事發時所任,下同)Robert O.Wilson證人在法庭對檢察方、辯護方質證的回答到1948年4月9日中支那方面軍⑩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將最終辯論的檢辨雙方在法庭的26次折衝。內容主要為:(1) Wilson、紅卍字會副會長許傳音、南京市民(以下為南京市民者不另註明)陳福寶、金陵大學教授Miner Searle Bates、中國陸軍軍醫部(原文如此)上尉梁廷芳、松井石根、無所任公使伊藤述史,中支那方面軍參謀副長武藤章大佐、基督教聖公會牧師John Gillespie Magee、中支那方面軍參謀中山寧人少佐、日本駐南京大使館參事官日高信六郎、上海派遣軍法務部長塚本浩次高等官、日本外務省東亞局長石射豬太郎、第十六師團參謀長中澤三夫大佐、上海派遣軍參謀長飯沼守少將、上海派遣軍特約隨從人員岡田尚證人先後出庭回答檢方、辨方或檢辨雙方的質證。 (2)檢察方先後宣讀尚德義、伍長德、陳福寶、梁廷芳、金陵大學教授Lewis S.C.Smythe、基督教青年會幹事George A.Fitch、陳瑞芳、美國基督教佈道團牧師James H.McCallum、孫永成、李滌生、羅宋氏、吳經才、朱帝翁•張繼祥(同件)、王康氏、胡篤信、王陳氏、吳著清、殷王則(11)、王潘氏、吳張氏、陳賈氏的書面證詞及松井石根1937年12月19日聲明、向哲濬等代表檢方提出的日軍殘虐行為(12)報告、徐希淑編《南京安全區文書》(13)、南京地方法院檢察官報告中魯甦的證詞,南京地方法院檢察處《敵人罪行調查報告》、美國駐南京大使館1937年12月至次年有關南京狀況的報告、武藤章訊問記錄、第73屆議會貴族院預算委員會議事錄摘要(大藏公望問、木戶幸一答)。 (3)法庭先後就松井石根1937年12月18日聲明、同年12月9日“勸降文告”、同年12月1日《ジャパン•アドバ-タィサ-》刊載的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部長的談話、同年11月16日《東京日日新聞》關於松井石根對Jaquinot等設立南市難民區“援助”的報導作為被告方證據是否受理進行討論(結果均被法庭駁回)。 (4)辯護律師先後宣讀日高信六郎、塚本浩次、中山寧人、石射豬太郎、文部大臣木戶幸一、第三師團野砲兵第三聯隊第一大隊觀測班長大杉浩少尉、第九師團山砲兵第九聯隊第七中隊代理中隊長大內義秀少尉、第九師團第三十六聯隊聯隊長脅坂次郎大佐、步兵第十九聯隊第一大隊大隊長西島剛少佐、中澤三夫、飯沼守、第十軍法務部長小川關治郎高等官、上海派遣軍參謀榊原主計少佐、大亞細亞協會理事下中彌三郎證人的書面證詞及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委員長John H.D.Rabe函(摘要)、James H. McCallum書面證詞(摘要)、美國駐南京大使館副領事James Espy報告、1938年2月4日正午美國駐日本大使Joseph Clark Grew給美國國務院的電報、松井石根1937年12月18日“訓示”、上海派遣軍“金山寺告示”、松井石根所建觀音堂戒壇照片、松井石根1937年12月18日聲明及“告中華民國人士書”。 (5)檢方和辯方陳述和辯論。

未宣讀的法庭證據計有:(1)據南京慈善團體及魯甦報告的敵人大屠殺。 (2)崇善堂埋葬隊埋葬屍體數統計表。 (3)世界紅卍會南京分會救援隊埋葬班埋葬屍體數統計表。
不提交書證計有:檢察方:(1)《東京日日新聞》百人斬競爭報導。 (2)岡田勝男宣誓口供書。 (3)黃俊鄉證人的書面證明。 (4)Frank Tilman Durdin的陳述。 (5)《由日本軍在南京屠殺支那地方民眾、解除武裝的軍人及南京紅卍會埋葬屍體的實況》。 (6)《民國廿六年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埋葬處攝影》。 (7)對人類之罪——中國確認書(中國政府信函原件)。辯護方:(1)1937年12月10日《大阪朝日新聞》摘要(《負傷兵拒之門外,非人道之極的支那軍》)。 (2)1937年 12月10日《大阪朝日新聞》摘要(《讓外國軍事專家吃驚的支那軍的瘋狂大破壞》)。 (3)1938年4月16日《大阪朝日新聞》北支版摘要(《處理屍體工作——面臨惡疫猖狂期、防疫委員會大活動》)。
判決計有:(1)第二章=法(1948年11月4日宣讀)之(ハ)起訴書部分。 (2)第八章=“通例的戰爭犯罪”之“南京暴虐事件”部分。 (3)第十章=“判定”之松井石根部分。 (4)印度代表Radhabinod Pal法官判決書之第六部=“在嚴密的意義上的戰爭犯罪”之二“'嚴密意義'上的戰爭犯罪、關於日本佔領下的諸地域的一般人的訴因第五十四及五十五”。
Ⅱ卷除解題和解說,收了4種文獻,計為:(1)H.J.Timperley編《戰爭是什麼——在中國日本軍的暴行》(14);(2)徐淑希編《南京安全區檔案》;(3)Lewis S.C.Smythe編《南京地區戰爭災禍——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都市及農村調查》;(4)《紐約時報》南京特派記者F. T.Durdin報導。
本書所收是首次為“南京事件”定讞時的依據,雖然就像東京審判本身從一開始即受到質疑和不滿(15)一樣,對這些依據怎麼看也向有歧義,但由於東京審判有著“國際”的權威名分,無論持維護、修正、反對何種立場,對東京審判的證據、結論都無法繞開。如果追溯日本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論爭,主要爭點幾乎都可以在東京審判中找到源頭。所以,即使今天隨著各種文獻的發掘,尤其是隨著爭論從法庭轉向“學界”(16)而多少有了從容探討的餘地,使對南京大屠殺的認識已有所深入,本書所收仍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2.《南京事件資料集》
日本“南京事件調查研究會”(17)編譯,青木書店1992年10月出版。是集分上下兩卷,上卷為“美國關係資料編”,下卷為“中國關係資料編”。
上卷包括:解說、第Ⅰ編“文書記錄的南京事件”、第Ⅱ編“新聞報導的南京事件”、附錄“F. T.Durdin和Archibald T.Steele訪談資料”。其中第Ⅰ編計有:(1)南京空襲;(2)Panay號及Ladybird號事件;(3)南京的狀況;(4)南京國際難民區;(5)日本軍的殘虐行為。下卷包括:解說、第Ⅰ編“新聞報導的南京事件”、第Ⅱ編“著作資料所見之南京事件”、第Ⅲ編“遺體埋葬記錄”、第Ⅳ編“南京軍事審判資料”、附錄1“南京事件有關中文記事目錄”、2“主要中文資料集目錄”。
下卷主要取材於南京圖書館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料》、二檔館和南京市檔案館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檔案》、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南京保衛戰——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國民黨黨史會編《革命文獻》及《大公報》等報刊。
本書上卷所收多為首次結集(18),許多材料頗費搜尋,得之不易。而且,作為中日之外的“第三者”,至少不會因為“民族感情”作左右袒,這是本編的特殊意義所在。
3.《南京事件京都師團關係資料集》
井口和起、木坂順一郎、下里正樹編,青木書店1989年12月出版。是集收摘了日軍京都第十六師團福知山步兵第二十聯隊士兵增田六助、上羽武一郎、北山與、牧原信夫、東史郎日記和曾田六助手記、上羽武一郎筆記及第二十聯隊第四中隊陣中日記、第十二中隊答後方。另有解題兩篇:井口和起“京都戰爭展覽運動和資料發掘”及下里正樹“南京攻略和下級士兵”。
第十六師團是日軍攻占南京的主力部隊之一,本編是日軍士兵戰時原始記錄第一次較集中的公開(19)。作為肇事者的“不打自招”,誠如編者之一的下里正樹所說,從中可以切實具體的感受到南京大屠殺的“直接間接原因”(20)。
4.《記錄南京大屠殺的皇軍士兵們》
小野賢二、藤原彰、本多勝一編,大月書店1996年3月出版。是集收錄了日軍仙台第十三師團山田支隊(21)會津若松步兵第六十五聯隊“齋藤次郎”等(22)16名、越後高田山砲兵第十九聯隊“近藤榮四郎”等3名下級軍官和士兵的19篇日記。
本編主要編者小野賢二先生不在學界(自稱“勞動者”),常年的採訪、收集都在工餘進行,殊為不易(23),令人感動。本編的最大意義是證明了戰時報導的“兩角部隊”(24)在幕府山俘虜的一萬四千名中國官兵大部分遭到了槍殺(25)。
5.《南京戰•尋找被封閉的記憶——原士兵102人的證言》
松岡環編,社會評論社2002年8月出版。是集所採“證言”,包括日軍金澤第九師團(6人)、名古屋第三師團(5人)、熊本第六師團(1人)、第三十八部隊第二碇泊所(4人)、第三艦隊第十一戰隊(1人)士兵,主要是十六師團的士兵(85人),其中又以第三十三聯隊最多(59人)。
在迄今所有訪談中本編受訪人數最多。松岡女士及旅日華商林伯耀先生等在“逆境”中所作的努力,值得讚賞,但在日本屠殺派中也有不同評價(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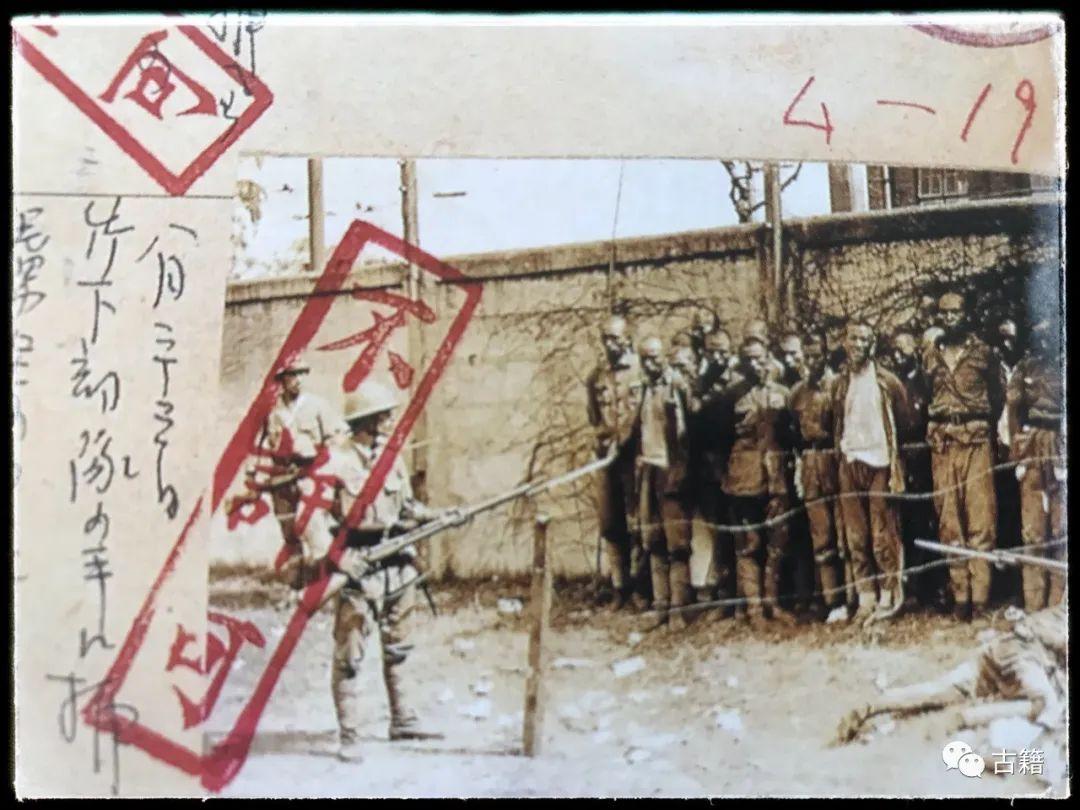
二、中間派
6.《南京戰史資料集》
南京戰史資料編集委員會編,偕行社1989年11月出版。是集分日記、作戰命令、通牒•訓示•作戰經過概要•戰時旬報•戰鬥詳報•陣中日誌、中國方面情報、第三國情報、戰史研究筆記、戰時國際法七部分,最重要的是前三部分。
日記部分收錄了《松井石根大將戰陣日記》、《松井大將〈支那事變日誌拔粹〉》、《陸軍大將畑俊六日誌(要約)》、《杉山(27)書簡》、《飯沼守日記》 、《上村利道日記》、《中島今朝吾日記》、《金丸吉生軍曹手記》、《佐佐木到一少將私記》、《山崎正男日記》、《木佐木久日記》、《伊佐一男日記》、《折小野末太郎日記》、《折田護日記》、《前田吉彥少尉日記》、《井家又一日記》、《初年兵之手記》、《水穀莊日記》、《牧原信夫日記》、《林(吉田)正明日記》、《增田六助日記》、《海軍軍醫大佐泰山弘道著上海戰從軍日誌》。作戰命令部分包括中央(參謀本部、大本營等)、方面軍、軍直至師團、旅團的命令。第三部分收入了包括從中央到基層(大隊及中隊)的相關文獻。
本編由日本舊軍人團體編輯,編委除板倉由明(著有《真相是這樣的南京事件》)外都是舊軍人。如題所示,嚴格說本編不是“南京大屠殺”或“南京事件”的資料集,但因戰爭結束之際和東京審判之前日本自上而下兩次命令燒毀戰時文件,相關文獻已十不存一,所以即使“戰史”方面的零散文獻對從更廣泛方面了解日軍的所作所為還是有價值。本編所收日軍官兵日記的特點是包括最高長官以下的各個層級,與屠殺派所編資料集悉為士兵和下級軍官不同。
7.《南京戰史資料集》Ⅱ
南京戰史資料編集委員會編,偕行社1993年12月出版。是集主要內容為日記,也有部分其他文獻。本編標以“Ⅱ”,但似非編輯前編時的預定,因前編未標“Ⅰ”,且內容稍有重複。計有:《松井石根大將戰陣日記》(全文)、《松井大將〈支那事變日誌拔粹〉》(與前編相同)、《陸軍大將畑俊六日誌(要約)》(同前)、《杉山書簡》(同前)、《松井指揮官、山本實彥對談》、《河辺虎四郎少將回想應答錄》、《對支那中央政府方策》、《上村利道日記》(前編自12月1日始,本編自8月15日起)、《山田栴二日記》、《兩角業作手記》、《荒海清衛日記》、《大寺隆日記》、《菅原茂俊日記》、《步兵第三十六聯隊第十二中隊陣中日誌》、《步兵第四十七聯隊陣中日誌》、《戰車第一中隊行動記錄》、《太田壽男供述書》、《梶谷健郎日記》、 《俘虜處理規則》、《支那事變關係公表集》、《大本營陸軍部西義章中佐的報告》、《外國的報紙》、《南京、上海、杭州國防工事的構想、構築和作用》、《南京城复廓陣地的構築和守城戰鬥》、《“從軍是走路”——佐藤振壽手記》、《“南京!!南京!!新聞匿名月評》。
日本右翼每為戰時文獻燒毀“遺憾”,似乎否則即可為日軍“洗冤”(28)。其實當時日本軍政當局和涉案人是把這些文獻視為隱患,惟恐不能悉數清除的。比如松井石根的日記明明還在,在東京法庭上他卻謊稱已經燒毀。本編所收松井日記“全文”(29),由日本防衛研究所戰史部研究員原剛(小屠殺派)在前編出版後“發現”。此編及前編所收日軍高級將領的日記,對全面了解“南京事件”的背景,了解日軍最高層尤其是中支那方面軍和上海派遣軍的決策十分重要。

三、虛構派
8.《紀聞•南京事件》
阿羅健一編,圖書出版社1987年8月出版。共收訪談錄35篇及補遺。訪談錄計為:《上海派遣軍參謀大西一大尉的證言》、《松井司令官隨員岡田尚氏的證言》、《上海派遣軍特務部成員岡田酉次少佐的證言》、《東京日日新聞金澤喜雄攝影師的證言》、《報知新聞二村次郎攝影師的證言》、《大阪每日新聞五島廣作記者的證言》、《第十軍參謀吉永樸少佐的證言》、《第十軍參謀谷田永大佐的證言》、《第十軍參謀金子倫介大尉的證言》、《東京日日新聞鈴木二郎記者的證言》、《東京日日新聞佐藤振壽攝影師的證言》、《同盟通訊社新井正義記者的證言》、《同盟通訊社映畫部淺井達三攝影師的證言》、《東京朝日新聞足立和雄記者的證言》、《東京朝日新聞上海支局次長橋本登美三郎氏的證言》 、《報知新聞田口利介記者的證言》、《都新聞小池秋羊記者的證言》、《讀賣新聞攝影技師樋口哲雄氏的證言》、《同盟通訊社無線電技師細波孝氏的證言》、 《砲艦勢多號艦長寺崎隆氏的證言》、《福岡日日新聞三苫乾之介記者的證言》、《海軍從軍繪畫通訊員住谷盤根氏的證言》、《砲艦比良號艦長土井伸二中佐的證言》、《外務省情報部特派攝影師渡辺義雄氏的證言》、《大阪朝日新聞上海支局成員山本治氏的證言》、《讀賣新聞森博攝影師的證言》、《上海海軍武官府報導擔當重村實大尉的證言》、《同盟通訊社上海支社長松本重治氏的證言》、《福島民報箭內正五郎記者的證言》、《第二聯合航空隊參謀源田實少佐的證言》《企畫院事務官岡田芳政氏的證言》、《領事官補岩井英一氏的證言》、《陸軍報導班成員小柳次一氏的證言》、《領事官補粕谷孝夫氏的證言》、《野跑兵第二十二聯隊長三國直福大佐的證言》。補遺交代了和上海派遣軍參謀松田千秋大佐等32位當事人聯絡的情況。其中有的本人拒絕採訪,有的因年高而為家人拒絕,有的在聯絡中去世,也有少數作了簡短回复。在拒絕受訪者中,認為南京大屠殺為“未有之事”談亦無益居多;少數則因懷疑作者的立場而不願談,如東京日日新聞記者淺海一男,事發時曾報導哄傳一時的“百人斬”(肇事者因此戰後被南京法庭判處死刑),在拒絕的同時特別說:“希望不要加入到否定這一'世紀'大屠殺的軍國主義的大合唱中去。”( 30)
9.《“南京事件”日本人48人的證言》
阿羅健一編,小學館2002年1月出版。本編是《紀聞•南京事件》的“文庫本”(31)。編排作了調整,除某些訪談的少量刪節,全刪了同盟社上海支局長松本重治的證言,新增了新愛知新聞記者南正義、參謀本部庶務課長諫山春樹大佐、陸軍省軍務局軍事課編制班大概章少佐的證言(32)和櫻井よしこ的薦詞、出版方的“寫在文庫化之際”,阿羅重新撰寫了後記。櫻井稱此書為“南京事件”的“第一級資料”;阿羅的新舊後記的最大不同,是新後記特別強調日軍在南京只有對軍人的“處刑”,而沒有對平民的犯罪。
資料集方面還有完全譯自中國的現成資料或在中國的實地調查,如加加美光行、姬田光義譯《證言,南京大屠殺》(青木書店1984年第1版)、《南京事件現地調查報告書》(南京事件調查研究會、一橋大學社會學部吉田研究室,1985年),不再介紹。
資料集之外,另有單篇文獻、日記、回憶,訪談等。單篇資料數量龐大,大多內容零散,有些較集中的國內已廣泛報導(如中譯早於原文出版的《東史郎日記》(33)、已為國內摘譯的《日中戰爭從軍日記——一個輜重兵的戰場體驗》(34)),有些是國外的譯本(如平野卿子譯的拉貝日記《南京的真實》(35)),所以,在此只擇要介紹三種在日本國內未引起足夠注意的材料,其餘在下篇中引及:
1.《日軍第十軍法務部日誌》
載高橋正衛編《續•現代史資料》六“軍事警察”,みすず書房1982年版。本編內容基本未涉及南京,日本各派也都未予關注。但如前已述,日本戰敗時曾大量焚毀日軍文獻,第十軍法務部日誌是日軍“僅存”(36)的法務部日誌,而第十軍所轄各部隊又都與“南京事件”有關(第六、第一百十四師團是直接攻擊南京的主力部隊,第十八師團和國崎支隊(37)為切斷外部對南京的增援和南京守軍的撤退分別攻占蕪湖和浦口) ,所以第十軍在攻占南京前後的表現,不僅對認識日軍軍風紀的一般狀況有重要價值,對第十軍——上海派遣軍也可以推求——進入南京後的表現尤其可為重要參照( 38)。
2.《中支那方面軍軍法會議日誌》
載同上。中支那方面軍未設法務部,軍法會議存在了不足一月。日誌記載的案例以第十軍為主,也有少量上海派遣軍“軍中逃亡”等案,可作為前志的補充。
3.《一個軍法務官的日記》
此本晚近才發現,作為第十軍法務部長,小川關治郎的日記正好是可以和第十軍法務部日誌互校的別本。小川日記除了實錄第十軍軍風紀的本來意義之外,還有二點特別意義,即:一,證明小川在東京審判時為辯護方提供的證詞不實(下將詳及);二,證明日軍軍方戰時記載對事實已有損益(39)。

下篇
無庸否認,南京大屠殺在日本的由來已久的爭議從根本上說和“立場”有關,不過第一手文獻不夠充分不能不說也為“見仁見智”留下了余地。那麼,日本現存的材料可以證明什麼?可以證明到什麼程度?哪些還有疑問?哪些還不能證明?以下擇要作一簡括。
一
1.攻擊南京是上海派遣軍的預決還是“意外”
“八一三”出於中國“先發製人”,現在已為國內不少學者接受(40)。但日本派重兵來滬雖未佔著先機,卻也不是像日本流行觀點所說僅為了消極的“保護日本僑民”。消極說源於東京審判時為松井石根的辯護和松井的自辯(41)。此說在南京大屠殺論脈中的意義是:進攻南京並非事前計劃,而是戰事發展“迫不得已”的“意外”,因此南京即便有“少量”暴行也是環境使然的“偶然”。
不必否認,日軍在發兵時有過所謂“保護我居留民的生命財產和權益”的堂皇說辭,參謀本部也先後有過兩次製令線的限制(42)。但這不等於攻擊南京事出“意外”或“被迫”。如果我們將視界稍稍放寬,可以看到昭和後日軍“下克上”久成風氣,現地日軍“暴走”的常態化,也已非所謂“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可以比擬,有人稱日本其時已成現地軍“隨心所欲的機制”(43),並非誇張。從皇姑屯、柳條溝的爆炸到“滿洲國”的建立等一系列事件都由基層發動,事後中央都“不得不”追認,都是顯例。 “七七”後情況也是如此。當時陸軍省軍務課長柴山兼四郎大佐後來追憶他和參謀本部總務部長中島鐵藏少將向“支那駐屯軍”司令香月清司中將傳達中央“不擴大”方針時不僅被拒絕而且遭痛斥即是一個生動的例子(44)。從這一意義上說,有沒有中央成命並不能作為判斷日軍行為的恰當根據。

但我們說日軍進攻南京並非“意外”,確有實據,而不只是從一般情況的推導。日本舊軍人團體編輯出版的“戰史”資料《南京戰史資料集》有為日軍“正名”的意圖,但如前所說,此集中所收日軍高級將領日記對了解日軍的決策還是有價值。我們從《飯沼守日記》中可以看到,上海派遣軍尚未出發,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已明確表示:“應該放棄局部解決、不擴大方案”,“應斷然地用必要的兵力以傳統的精神,速戰速決。比起將主力使用於北支,更有必要使用於南京”,“應在短時間內攻占南京”(45),與東京審判時所說不得已完全相反。 《南京戰史資料集》Ⅱ所收《松井石根大將戰陣日記》新“發現”的10月之前的部分,更詳細記錄了松井的打算和心境。 8月14日松井從陸相杉山元大將處獲知將統轄上海派遣軍時,即對軍方尤其是參謀本部未將“中支”作為主戰場“不勝憂慮”。次日的日記中記下了他的“痛感”:“應盡快斷乎以鐵鎚使支那政府覺醒”。 16日他本想說動參謀本部第一部長石原莞爾少將,話不投機,轉而遊說參謀本部第二部長本間雅晴少將和杉山陸相,表示:“應以攻略南京為目的”,“有必要一舉覆滅南京政府,因而對南京政府的壓迫除了依靠武力的強力外,加上經濟、財政會更有效”(46)。此時所說的“目的”,也是松井所轄的上海派遣軍和再後成立的第十軍的不變目標。所以攻占南京的日軍中央命令雖較晚發出,對上海派遣軍而言則是始終一貫的方針。
2.日軍是否曾有“和平”進入南京的打算
日本有一個長期以來未受辨別的說法,即聲稱日軍兵臨南京城下時,12月9日曾空投勸降文告,要求中方在次日中午前作出答复,中支那方面軍參謀長塚田攻少將偕參謀公平匡武中佐、中山寧人少佐和岡田尚在中山門外等待至下午1時,未見回复,才向南京發動進攻(47)。今天更將勸降書發揮為“按照國際法”的“和平開城勸告文”(48)。此說在日本“虛構派”“中間派”中十分流行,其潛台詞,用渡部升一的話說:“如果這時中國投降,將什麼都不會發生。”渡部並聲稱:“率領國民政府的蔣介石並沒有向世界傾訴南京大屠殺,原因就在這裡”(49)。此篇勸降文告“虛構派”看得很重。 《真相•南京事件》便以《拉貝日記》未記此事作為日記不實的一個根據(50)。以不記某事作為不實根據的不經,無須一辨,但9日到10日的期限日軍是否“和平”地等待了一天——從中可見中國軍隊如果撤守日軍有否“不加以攻擊”的誠意,則值得澄清。
據當時在寧的中外人士的記錄,查明9日到10日日軍是否停止攻擊並不困難。 《拉貝日記》 12月9日一開始就記載了“空襲從一大清早就持續不斷”。日軍轟炸後來也未停頓。拉貝在第二天續記“隆隆的砲火聲、步槍聲和機槍聲從昨天晚上8時一直響到今天凌晨4時”,“今天城市全天遭到了轟炸”(51)。當日日記還記載了前一夜(9日晚)日軍差一點佔領光華門及推進到長江邊自來水廠的情況。 《魏特琳日記》12月9日記:“今晚,當我們參加記者招待會的時候,一顆巨大的砲彈落在了新街口,爆炸聲使我們都從座位上站了起來。”次日日記記載了“夜裡槍砲聲不斷” (52)。費吳生(George A.Fitch,亦多音譯成費奇)的南京“日記”記於“1937年聖誕節前夕”,起始時間是12月10日,其中10日記:“重砲轟擊著南京南部城門,炸彈在城內開花。”(53)此條記載雖未註明具體時間,難以判斷是否在“勸告”的期限正午之前,但與上引互參,可以作為一個證據。 12月9日日本的“勸告”發出後,日本並未停止進攻,在國人的記載中也可以看到。蔣公穀在《陷京三月記》中記:“(9日)聽說敵人已攻到麒麟門一帶,逼近城垣了。槍砲聲較昨日更來得密集而清晰。城南八府塘,已遭到敵人的砲彈。……夜間十二時後,炮聲轉烈,都向著城中射擊;窗外不時掠過一道道的白光。”(54)敵至麒麟門的“聽說”,有日軍記錄可證(55)。次日上午日軍的攻擊《陷京三月記》中有更詳細的記錄(56)。從這些互不相關的中外人士的紀聞,我們可以看到日軍的言行完全不一:所謂的“勸告”發出後,南京不僅沒能免遭攻擊,反而因日軍的到來,在空投的炸彈之外增加了大砲的直接轟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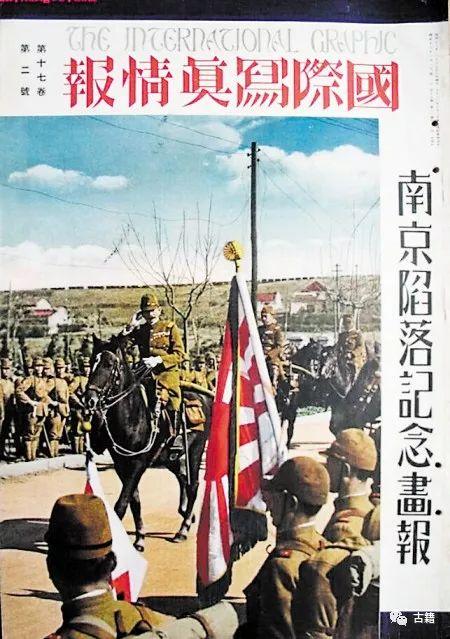
日軍寡信如此,虛構派為什麼還每每提出?或許“虛構派”以為日軍高層意在“和平”,轟炸只是上命未能下達。那麼,就讓我們再來檢查一下日軍自己的記錄,看看是不是有什麼“誤會”。日軍第九師團在9日下午4點,也就是“和平開城勸告”發出之後,發布瞭如下的命令:
二、師團利用本夜之黑暗佔領城牆
三、命兩翼部隊利用本夜之黑暗佔領城牆,命左翼隊長將輕裝甲車兩小隊歸右翼隊長指揮
四、命砲兵部隊根據所需協助兩翼部隊作戰
五、命工兵部隊主要協助右翼部隊戰鬥
六、命其餘各部隊繼續完成之前任務(57)
等待“和平開城”反應的背後,原來是“利用本夜之黑暗佔領城牆”(58)!這樣的行動是否僅限於第九師團,只是個“偶然”?讓我們繼續檢查日軍的有關材料。據第六師團“戰時旬報”記:
9日夜半,第一線部隊決行。為了立即利用夜襲成果,師團長上午六時至東善橋,命令預備隊並砲兵隊向鐵心橋前進。 (59)
第六師團也是“夜襲”。第一百十四師團的“作戰經過”記:
9日夜,秋山旅團突破將軍山附近敵人陣地,急追敵人。 10日晨,佔領雨花台附近陣地,達到敵前,並立即開始進攻。 (60)
秋山旅團即第一百十四師團屬下的步兵第一百二十七旅團。在師團的“戰鬥詳報”和“戰時旬報”中對9日晚到10日正午的不間斷攻擊有詳細記載(61)。不僅是師團一級的文獻,基層也不乏有關的記載。如屬於第十六師團的步兵第三十三聯隊,在“戰鬥詳報”中記:
聯隊12月9日夜按照師團“命步兵第三十三聯隊(缺第一大隊及第五、第八中隊)作為右翼隊從本道(含本道)北側地區攻擊前進,和右側支隊的戰斗地域五旗蔣王廟、玄武湖東方五百米南京城東北角連成一線(線含右方)”之命令,光榮地沐浴著接受攻擊紫金山一帶高地的重大任務的將士,鬥志愈益昂揚。 (62)
從上可見,日軍在“和平開城勸告”發出後,藉著夜幕發動攻勢並未稍息,並未信守等待中方答复的承諾,源自東京審判的所謂中方逾期未作回答,“日軍才開始總攻擊”云云,完全不合事實(63)。
3.南京周圍有沒有被日軍屠殺的大量屍體
近30年來,特別是近10年來,隨著一些重要史料的重見天日,完全否定日軍暴行已日益困難,日本有些人不得不作出戰略調整,將一些較“次要”的罪行,推出任斬,但對關鍵的、具有標誌意義的“大屠殺”則仍絕口否認,半步不讓。虛構派大井滿的態度就是這種丟卒保車例子的典型。他在《編造出來的南京大屠殺》中說:“當然,我並不是說日本軍完全沒有不法行為。七萬人的軍隊什麼都不發生,沒有這樣的道理,這是誰都會認為的常識。大西參謀給強姦兵重重的耳光,並抓至憲兵隊,這樣的事無疑在各個地方都有。”(64)而在《諸君! 》的問卷調查中,他在第一項被殺人數的選擇答案中填了“12”(65),“12”是表明“無限地接近於0”。
南京的被殺屍體最終通過掩埋、焚燒、棄於江中等途徑清除乾淨,但在相當一段時間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這是否認南京屠殺的最大障礙,也是虛構派著意“辯駁”的一個關鍵。松井石根的專任副官角良晴少佐,晚年撰文《支那事變最初六個月間的戰鬥》,因文中談到日軍的大規模屠殺,生前未被刊出(後刊於舊軍人團體主辦的《偕行》 1988年1月號)。因為角氏的特殊身份,所以他的回憶一經披露,立即引起了爭議。其中最大的爭點是“下關附近的十二、三萬屍體”(66)。據角良晴說,造成這些死者的真兇是第六師團,而下達屠殺令的是上海派遣軍參謀部第二課參謀長勇中佐,長勇下達命令時他也在場(67)。對此,“虛構派”“中間派”一致質疑。 《南京戰史》以為角良晴的回憶“多有矛盾,缺乏信憑性”(68)。 《南京戰史資料集》所附“戰史研究筆記”也認為:“角氏的誤解、偏見、記憶失誤不勝枚舉”(69)。然而,角良晴所說並非孤證。
松井石根本人的日記就有一條證明。松井日記12月20日記:
朝10點出發,視察挹江門附近的下關,此附近仍是狼籍之跡,屍體等仍盡其遺棄,今後必須清理。 (70)
第十軍參謀山崎正男少佐在12月17日日記中有這樣的記載:
到了揚子江邊的中山碼頭。 ……河岸遺棄有無數死屍,被浸於水中。所謂“死屍累累”也有不同程度,這個揚子江邊才真是死屍累累,如果將之放在平地上,真的可以成為所謂“屍體山”。但看到的屍體已經不知多少回,所以已不再有一點吃驚。 (71)
“中山碼頭”一帶,與角良晴所說正是同地。
“支那方面艦隊”司令部軍醫長泰山弘道海軍軍醫大佐12月16日坐水上飛機到南京,下午2時,他與艦隊“機關長”、“主計長”等一行去戰地“參觀”,他在當日日記中記:
從下關碼頭起,在修建的一直線的廣闊的道路上開著,路面上散亂著步槍子彈,宛如敷著黃銅的砂。路旁的草地散著活生生的支那兵的屍體。
不久,從下關到通往南京的挹江門,高聳的石門下是拱形的道路,路高約三分之一埋著土。鑽入門,從下關方面就成了一條坡道。汽車徐徐前進,感覺是開在充滿空氣的橡皮袋上緩緩的向前。這輛汽車實際是行駛在被埋著的無數敵人屍體之上。很可能是開在了土層薄的地方,在行進中忽然從土中泌出了肉塊,淒慘之狀,真是難以言表。 (72)
此處之“下關碼頭”到“挹江門”一帶,與角良晴所說也是同地。從這幾位無關者的相同記載,此事之確鑿不移,不應再有任何疑義。而且,不論其中有沒有平民,從江邊不是戰場來說,“死屍累累”至少是屠殺俘虜的結果。
《南京戰史資料集》所附“戰史研究筆記”中對角良晴所述中有一條特別予以“批判”。其謂:“'在橫陳著累累屍體的河岸道路上靜靜地走了兩公里。感慨萬千。軍司令官的眼淚嗚咽著往下流'的記述實在讓人吃驚。愛著中國,愛了中國的大將決不會在戰場的棄屍上行車。而且,車體低的轎車也決不能夠在這之上走兩公里。我以為,僅在這點上,完全是編造,誰都可以斷言。”(73)但這樣的“斷言”未免武斷。這不僅是因為有泰山弘道等(74)所說的“行駛”在“無數屍體之上”的支持,而且是因為這是一個反常理的事,編造是不會走這樣的險徑的。
屠殺在當時的廣泛程度,日軍官兵的記載有相當的反映。以下我們再來看一看泰山弘道在上引16日日記中接著的記載。
即將開出門洞進入南京一側,累累的敵屍成了黑焦狀,鐵兜、槍刺也被熏黑,用於鐵絲網的金屬絲和燒塌的門柱的殘木相重疊,堆積的土壤也燒成黑色,其混亂和令人鼻酸,無法形容。

門右首的小丘上,刻著“中國與日本勢不兩立”,顯示著蔣介石宣傳抗日的痕跡,接近市內,敵人遺棄的便衣蘭布棉襖,使道路像襤褸的衣衫,而穿著土黃色軍服,扎著神氣的皮綁腿,手腳僵直仰臥著的敵軍軍官屍體,也隨處可見。
上引只是泰山弘道到南京第一天所見的一個片段,他在南京的三日,每到一處,都遇到了大量屍體。如第二天(17日)早上,在下關的另兩處,看到了“累累屍體”,並親見一個“血流滿面”“求饒”的中國士兵被一“後備兵”(75)從身後近距離槍殺;上午在中山北路沿途看到“累累屍體”;下午與大川內傳七上海海軍特別陸戰隊司令等“視察”下關下游的江汀,看到“無數焦黑的敵人屍體”,又在江堤內看到“'嚐了日本刀滋味'的敵人屍體六七十具”。 18日,先在獅子林,看到“此處彼處都是敵人遺棄的屍體”;又在山麓的兵營外,看到“散落的屍體”;到了中山公園,又看到“散落的敵人屍體”(76)。
類似的事發時留下的第一手材料,最有力的證明南京周圍至少有大量中國軍人——當然不只是中國軍人,以下我們會述及——的屍體。那麼,這些屍體究竟是戰死者還是被屠殺的軍人呢?我們在探明這一日本爭論不休的“疑問”之前,先來檢查一下日軍高層有沒有下達過屠殺令。
4.在攻占南京過程中日軍高層有沒有下達屠殺俘虜的命令
日軍在攻占南京的過程中,對停止抵抗的中國俘虜進行了大規模的屠戮,這一暴行出自日軍高層的命令,還是僅僅是基層部隊的自發行為?由於現存的材料殘缺不全,給認識這一問題帶來了很大的困惑。日本虛構派因為不承認任何意義上的殺戮(77),當然矢口否認有過屠殺令,日本軍史學界的代表作“戰史叢書”和《南京戰史》也不承認或傾向於否認屠殺出自自上而下的命令(78)。
在現存史料中,有三條記載明確的涉及了屠殺令,即:第十六師團師團長中島今朝吾中將12月13日日記中所記:
因為原則上實行不留俘虜的政策,所以從開始即須加以處理。 (79)
第十三師團步兵第一○三旅團旅團長山田栴二少將12月15日日記所記:
就俘虜處理等事宜派遣本間騎兵少尉去南京聯繫。
得到的命令是全部殺掉。
各部隊都沒有糧食,令人困惑。 (80)
第一百十四師團步兵第六十六聯隊第一大隊戰鬥詳報所記:
八、下午2點0分收到由聯隊長下達的如下命令:
下記
1、根據旅團命令,俘虜全部殺死;
其方法為,以10數名捆綁,逐次槍殺,如何?
2、兵器集聚,待新指示下達為止派兵監視;
九、基於上述命令,命令第一、第四中隊整理集聚兵器,派兵監視。
下午3點30分,集合各中隊長交換處決俘虜的意見。結果決定各中隊(第一、第三、第四中隊)等份的分配,以50名一批由監禁室帶出,第一中隊在露營地之南谷地,第三中隊在露營地西南方凹地,第四中隊在露營地東南谷地進行刺殺。
但應注意監禁室周圍需派兵嚴重警戒,帶出之際絕對不能被感知。
各隊均在下午5時準備結束,開始刺殺,至7時30分刺殺結束。
向聯隊報告。
第一中隊變更當初的預定,欲一下子監禁焚燒,失敗。
俘虜已看透因而無所畏懼,在軍刀面前伸出頭,在槍刺面前挺著胸,從容不迫,也有哭叫哀嘆救助的,特別是隊長巡視之際,哀聲四起。 (81)
因為這三條材料出自事發當時,屬於“第一手”,對複原屠戮俘虜是否出自命令有特殊的價值,所以日本虛構派和部分中間派不惜筆墨,詳加“論證”,號稱中島和山田的記載與屠殺令無關,而第六十六聯隊第一大隊戰鬥詳報的屠殺記錄從時間和內容兩方面看都與事實相違背,因此是編造。
我曾通過廣徵事發當時的相關文獻,參以當事人事後的回憶,證明上述記載就是屠殺令的明證(82)。其中主要論據為:一,第十六師團所轄第三十旅團黎明前發布的“各隊在有師團[新]指示前不許接受俘虜”的命令(83)與中島日記的精神一致,而之所以肯定此命令指的是屠殺俘虜,是因為有第三十旅團下屬第三十八聯隊副官兒玉義雄少佐有關此項命令的如下回憶:
接近於南京一、二公里,在彼我相雜的混戰中,師團副官通過電話傳來了師團的命令,'不許接受支那兵投降,處理掉',居然會下這樣的命令,令人感到震驚。師團長中島今朝吾中將是有人格魅力的豪快的將軍,但這一命令無論如何都不能讓人接受。對於部隊來說,實在讓人吃驚和困惑,但作為命令不得不往下向大隊傳達,以後各大隊沒有就此事報告。 (84)
兒玉的回憶出於中島日記引起爭議之前,不可能已有針對性的問題意識,所以他所說的“不許”應是三十旅團“不許”的最直接、最明確的證明。從中島今朝吾日記到三十旅團命令到兒玉義雄回憶,師團、旅團、聯隊,“首尾完具”,一脈相傳,中島今朝吾日記中屠殺令記載之可靠,無復存疑的餘地。二,山田日記不僅“文脈”毫無捍格之處(85),而且有屬於第一○三旅團的第六十五聯隊在海軍碼頭附近和上元門以東四公里處的大量屠殺俘虜的事實為證(86)。三,丁集團(第十軍) 13日上午8時30分發布“殲滅南京城之敵”(87),所部第一一四師團接命後於9時30分下達“應使用一切手段殲滅敵人”的命令(88),所部第一二八旅團接命後於12時發出“不惜一切手段殲滅敵人”的命令(89)(第六十六聯隊的直接頂頭上司是一一四師團所轄的一二七旅團,該旅團記載已焚毀,屬於同師團的一二八旅團當時也在南京地區,所傳達的命令應該一致),第六十六聯隊戰鬥詳報所記下午2時接到的命令正是“順理成章”的,完全沒有虛構派所說的時間和內容上的抵牾。所以不論當時上級命令是否明確,但六十六聯隊接命後的屠殺確實是在上級命令下的行動。
綜上所述,可以下一個肯定的結論:日軍在攻占南京的過程中屠殺的大量俘虜,不是所謂“一部分官兵造成的突發、散發的事件”(90),而是由現地日軍自上而下的命令造成的。雖然今天已無法復原或無法完全復原攻占南京的方面軍和軍一級的有關俘虜命令的真相(91),但至少可以肯定,日軍在師團一級確實曾下達過屠殺令。
5.南京城周邊的大量中國軍隊屍體是戰死者還是被屠戮的俘虜
日軍下達過屠殺令,不僅從殘存文獻的“文脈”中可以發現,關鍵還是因為如前所述有南京周邊地區大量中國軍人死亡的事實根據。因此日本除了大屠殺派的少數人,都特別強調南京城外的屍體死於“戰鬥”,而非屠戮。但梳理現存的日軍各級戰報和陣中日誌的記載,可以看到,在上海派遣軍和第十軍“徹底掃蕩”和“殲滅”“敵軍”的命令下,日軍許多部隊的所謂“殲敵”,實是屠殺俘虜。
隸屬於上海派遣軍第九師團的步兵第七聯隊,在12月7日—13日的“虜獲表”中“俘虜”無一人,而“敵人棄屍”505具(92),就當時投降接踵而至的情況說,無一活口,一定是因為第七聯隊“不留俘虜”。在第七聯隊12月13日—24日《南京城內掃蕩成果表》之二中,“敗殘兵”的“刺射殺數”達6670人 (93),而俘虜也沒有一人。 《步兵第七聯隊作戰命令甲第一一一號》明確命令“將敗殘兵徹底地捕捉殲滅”(94)。 “殲滅”之意可含俘獲,但將以上命令和結果兩相對照,第七聯隊在攻打南京以及城破後在掃蕩中的“殲滅”指的是肉體上消滅,應該沒有疑問。而且13日南京失陷後中國軍隊已放棄抵抗,被殺人數反而大大超過了之前,除了屠殺俘虜,也難以有其他解釋。
上海派遣軍第十六師團是進攻南京的主力部隊之一,其屬下步兵第三十三聯隊,在《南京附近戰鬥詳報》中稱:
(13日)下午2時30分,前衛的先頭部隊到達下關,搜索敵情的結果,發現揚子江上有無數敗殘兵利用舟筏和其他漂浮物流往下游,聯隊立即組織前衛及高速炮對江上敵人猛烈射擊,經二小時殲滅敵人約2000。 (95)
在同一詳報的第三號附表的“備考”中記錄了12月10日—13日包括“處決敗殘兵”和“敵人棄屍”兩項的屍體6830具(96)。同屬於第十六師團的步兵第三十八聯隊奉命對城內“徹底掃蕩”, 12月14日的《南京城內戰鬥詳報》的附表雖未如第三十三聯隊、第七聯隊等詳列“敵人棄屍數”或“刺殺敵人數”,但在“(五)”中明確記載了“全殲敵人”(97)。
隸屬於第十軍的第一百十四師團,在12月15日戰鬥詳報“附表第三”中記“敵人棄屍”共6000具,而在“附表第一”日軍傷亡之一、二、三分錶中死亡者合計為229人。
隸屬於第一百十四師團的步兵第六十六聯隊第一大隊,情況也相仿,12月12日攻入南京前日,“斃頑強抵抗之敵兵700人”,而自己隻死了9人(98)。同大隊在12月10日—13日共死17人,而被殺之“敵”則多達80倍以上,達到約1400人。
隸屬於第十軍第六師團的步兵第四十五聯隊第十一中隊在江東門的“遭遇戰”中“斃敵”3300人,而己方死傷相加僅80人。不僅在江東門,據第六師團“戰鬥詳報”記,第四十五聯隊第二第三大隊、第十軍直屬山砲兵第二聯隊之一部、第六師團騎兵第六聯隊之一部在從上河鎮到下關的整個戰鬥中,不僅以十分之一的兵力擊敗了中國軍隊,而且“斃敵”11000人,而己方“戰死”僅58人,約190比1(99)。
上引材料有兩點非常值得注意,一是只有“敵人棄屍”而沒有俘虜,一是“敵人棄屍”數量與日軍死亡之比例極其懸殊。在對壘的兩軍中出現這樣的情況,只有兩種可能,一是武器裝備差距過大,一是一方是已放下武器只能任人宰割的俘虜。當時是哪一種情況,因材料俱在,並不難徵明。比如上述第四十五聯隊的江東門之戰,不僅是“零距離”的“白刃戰”,而且又持同樣的武器(100)。上海派遣軍參謀副長(副參謀長)上村利道大佐,12月26日參觀挹江門南側高地的防禦設施及富貴山砲台,對地下掩體設施的“規模壯大”“深為感嘆”。同是這位上村利道,在次年 (1938年)1月6日去第十六師團參觀“虜獲兵器試驗射擊”後,在當日的日記裡留下了這樣的記錄:
下午作為殿下的隨行去16D(“殿下”指上海派遣軍司今朝香宮鳩彥中將,“D”為師團之代碼——引者)視察虜獲兵器的射擊。自動步槍、步槍、手槍、LG、MG(LG指輕機關槍,MG指重機關槍——引者)、火砲等良好的裝備,決不亞於我軍的兵器,令人感懷。 (101)

參謀本部第三課課員二宮義清少佐在赴中國考察後寫的“視察報告”中說:“在近距離戰鬥所用武備上,[日軍]和中國軍隊相比,不論在資質還是在數量上都處於劣勢。”(102)上海派遣軍10月在寶山作戰時,24厘米榴彈砲、30厘米臼炮多次發射出的砲彈都不爆炸,11月渡過蘇州河後,24厘米榴彈砲多次在管內爆炸。不僅重武器,輕武器日軍更沒有明顯的優勢。日軍攻打上海前任參謀本部支那課長、戰爭爆發後任第二十二聯隊聯隊長的永津佐比重大佐,曾因舊式手榴彈質量低劣,每有“不發彈”(擲出後不爆炸),向上海派遣軍參謀大西一大尉大光其火。無獨有偶,10月11日在寶山蕰藻浜一線作戰戰死的第一百一師團步兵第一百一聯隊聯隊長加納治雄大佐,在臨死前給師團參謀長的信中也提到手榴彈的“點火不充分”。普通武器如此,“高科技”武器亦如此。在開戰前夕從德國運至南京,裝備在雞鳴寺東側高地的電動瞄準的高炮,在當時是最先進的,曾使日本海軍航空兵感到很大的威脅。曾任步兵第二十聯隊第一大隊第三中隊中隊長的森英生中尉說:德國對中國的軍援使他感到日本受到的是“德國的打擊”(103)。引述此類材料並不是要證明中國軍隊武備已優於日軍,在總體上,尤其在飛機、重砲、坦克等重武器上,應該說日軍還是佔有優勢,但這種優勢的效果主要體現在攻堅戰和遠程破壞上;我在此想說明的只是:在近距離戰、肉搏戰、夜襲作戰上,日軍並沒有以一當十、以一當百的法寶。
所以,在南京周圍敵我雙方死亡之懸殊如此,除了對放下武器的俘虜的屠戮,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解釋。所謂“戰鬥”,所謂“零距離”的“白刃戰”云云,不過是各部隊為了邀功的飾詞。
南京城內外的大量屍體是被屠殺的俘虜,從軍方文獻中完全可以證明,同時,在第一線的下層官兵的記錄中則有許多屠殺俘虜的親身經驗和親歷見聞。我們不妨再略作徵引。步兵第四十五聯隊第七中隊小隊長前田吉彥少尉在12月15日日記記錄了當天“聽說”的所在大隊“後備補充兵”屠殺被押送俘虜的經過:
起因只是很小的事,因為道路狹窄,在兩側拿著上了刺刀的槍的日本兵,好像是被擠而落入還是滑入了水塘里。 [日本兵]勃然大怒,決定打還是罵,害怕的俘虜忽都避向了一旁。在那裡的警戒兵也跳了起來。所謂“兵者,凶器也”,哆哆嗦嗦端著刺刀槍叫著“這個畜生”,又是打又是刺。恐慌的俘虜開始逃跑。 “這樣不行”,於是邊叫“俘虜不准逃”“逃的話槍斃”邊開槍,當時一定是這樣。據說就是這樣的小誤解釀成了大慘事。 ……不能不說此事使皇軍形象掃地。為了隱蔽這一慘狀,這些後備兵終夜不停,到今晨才大體埋完。這是“非常”或極限狀態下以人的常識所無法想像的無道行為的實例。 (104)
這樣的“誤殺”,在當時屢有發生。所以究竟是不是“誤殺”,反而無須再論。
步兵第二十聯隊第三機關槍中隊牧原信夫上等兵在12月14日的日記中記:
上午八點半,一分隊協助十二中隊去馬群掃蕩。聽說殘敵因為斷了頓,搖搖晃晃地出來了,所以立即坐汽車出發。到達的時候,由步槍中隊解除了武裝的三百十名左右的敵人正等待著,迅速地全部槍殺後即回來。 ……在鐵路沿線分叉的邊上,有百餘名支那軍受到友軍騎兵的夜襲,全部被殺。 ……下午六時……抓到了六名敗殘兵,槍斃了。 ……今天一處異樣的風景是某處的汽車庫,敵人一百五六十名被澆上汽油燒死。但今天的我們已是看多少屍體都不會有任何反應了。 (105)
僅僅一日之中,牧原信夫和他所在的分隊就親眼所見和親自參加瞭如許的屠殺,這不是牧原信夫和他的同伴特別有“幸”,這只是當時在南京日軍整體的一個縮影。泰山弘道在12月19日日記中記:“據聞,最後堅守南京的支那兵,其數約有十萬,其中約八萬人被剿滅……。”(106)這“八萬人”中的大部分,當都是如上所述的“解除了武裝”者。
步兵第七聯隊第二中隊的井家又一上等兵在12月16日日記中記:
下午再次外出,捕來年輕的傢伙三百三十五人。 ……將此敗殘兵三百三十五人帶到揚子江邊,由其他士兵槍殺。 (107)
步兵第二十聯隊第三中隊第一小隊第四分隊的林(吉田)正明伍長,在日記中多次提到殺戮,其中24日中有將7千名“俘虜”帶到長江邊槍殺的記載,所謂“前記的俘虜七千名也成了魚餌”(108)。林正明的記載有兩點值得注意:一,上引泰山弘道、山崎正男等說16、17日在江邊已見大量屍體,“24日”仍在江邊殺俘,說明當時江邊已成了屠場;二,日本右翼將否定推屍入江作為否定江邊屠殺的一環(如果並無推屍入江之事,則大部分遺骨應該還在),而此處所謂“魚餌”,再一次證明日軍屠殺後屍體是推入江中的。
上引前田吉彥說的屠殺的細節,還是“據說”,井家又一在12月22日的日記中則向我們提供了一個親身經歷:
傍晚天快暗下來的下午五點,在大隊本部集合,準備去殺敗殘兵。一看,在本部院子裡,有一百六十一名支那人,正在等待神明,不知死之將至地看著我們。帶著一百六十餘名……,關入了這裡的一座房子。從屋子中帶出五人刺殺。 “嗷——”叫的傢伙,嘟噥著走著的傢伙,哭的傢伙,可以看到完全知道結局的喪膽相。戰敗的兵的出路就是被日本兵殺掉!用鐵絲綁著手腕,繫著脖子,邊走邊用棍打。其中也有唱著歌走著的勇敢的兵,有被刺後裝死的兵,有跳入水中阿噗阿噗殘喘的傢伙,有為了逃跑躲入屋頂的傢伙,因為怎麼叫也不下來,就澆上汽油用火燒,火燒後兩三人跳下來,被刺死了。
黑暗中鼓著勁刺殺,刺逃跑的傢伙,啪、啪的用槍打,一時這裡成了地獄。結束後,在倒著的屍體上澆上汽油,點上火,仍活著的傢伙在火中動了,再殺。後來燃起了熊熊大火,屋頂上所有的瓦片都落了下來,火星四散。回來的路上回頭看,火仍燒得通紅。 (109)
如果說前引木佐木久等的“義憤”還不失人道的意識,井家又一的立場則已無人性可言。
上引大多出自《南京戰史資料集》。此集出版者“偕行社”對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持否定態度,但因日軍在南京的暴行非如日本右翼所說只是“偶發”的個別行為,所以既要彙編史料,就不可能“乾淨”地不留痕跡。而散見於各種出版物的相關記載中,也可以看到不少類似的材料。
輜重兵第十六聯隊第四中隊第二小隊第四分隊第十九班的小原孝太郎,應徵時是千葉縣小學教師,他的日記從1937年9月1日入伍到1939年8月7日除隊,一日不缺。 1937年12月15日這樣記:
那一帶好像就是南京。翻過了山,在稍稍平坦的地方有個村莊。在這裡遇到了讓人吃驚的景象。在竹柵欄圍著的廣場中,多達二千名俘虜,在我軍的警戒裡小心地待著。讓人吃驚。後來才知道這正是攻擊南京時俘獲的俘虜。據說俘虜約有七千人。他們舉著白旗來,被解除了武裝。其中當然也有在戰鬥中俘獲的,各種情況都有。他們中也在軍服之外穿著便服的。在這裡先檢查一遍,以決定槍殺、役使還是釋放。聽說在後面的山里被槍殺俘虜的屍體,堆積如山。南京的大部分則好像已經過了清理。
12月17日日記中詳細記錄了在“徵發”時斬殺被發現的“敗殘兵”的血腥過程,同時還記有:
俘虜來了,正是昨天在那個村子裡的俘虜。拿著槍刺的約一個小隊穿插在中間,走啊走,不知有多少。跑過去問,說是有四千俘虜。都是三三、三八和二十聯隊在這一帶戰鬥俘獲的。護衛也都是這些聯隊的人。帶著這些東西派什麼用處?是去南京麼?有的說都槍殺,有的說帶到南京去服役。 ——總之,不知道,但俘虜原有兩萬人,處理的只餘下這些了。
18日前往南京途中,小原孝太郎也遇到了大量的屍體,在當天的日記中他這樣記:“屍體堆積如山,想像著[我軍]翻越屍體一路追擊敵人直至南京附近的樣子。”(110)這樣“如
文章為用戶上傳,僅供非商業瀏覽。發布者:Lomu,轉轉請註明出處: https://www.daogebangong.com/zh-Hant/articles/detail/Cheng%20Zhaoqi%20An%20Introduction%20to%20the%20Existing%20Historical%20Materials%20of%20the%20Nanjing%20Massacre%20in%20Japan.html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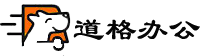

评论列表(196条)
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