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吕途著,法律出版社,2015
距离《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的出版才不过两年多,吕途又出版了她的第二本书《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这一次,吕途依旧保持着难以被忽略的双重身份。首先,她是受过西方学术训练的研究者和写作者,需要像任何社会学家或人类学家一样,和研究对象保持必要的距离;但同时,她长年生活在北京东五环外的打工者聚居区,在这个意义上,她又不同于一般研究者,她是研究对象的同路人。这种双重身份使吕途的写作任务变得非常特别:不仅仅分析性地呈现这个群体的文化实践和当代境遇,更是用知识生产的方式,参与到这个群体的历史过程之中,召唤新的主体性的形成,也试图呼唤劳动者在世界中的新的位置和新的身份政治。理解了吕途的这种“理论”和“实践”特殊的结合方式,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她的字里行间不仅有分析性的描摹,也充满了困惑、无奈甚至愤懑。作为对新工人群体在未来可能性的摸索的环节之一,吕途的写作应该被看作一个非常开放的文本,甚至是一个未完成的文本。她所探讨的新工人文化的问题,也同样应该被看作一个高度开放的问题,一个实践和探索的过程。
吕途为当代的新工人画群像,而“文化”是她描摹的关键。如果说,在她的上一本书中,她坚定地使用了“新工人”这样的概念,区别于“流动人口”“农民工”这样的称呼,把当代中国一大批劳动者的身份认同问题拉回到了阶级问题的层面。那么,在她的第二本书中,她则把有关劳动者主体性的讨论集中到了文化层面。无论是分析“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做什么样的人”,还是讨论“新工人文化的实践”,她所处理的新工人群体的文化问题,其本质都是探索劳动者主体性的形成。在吕途那里,文化不是仪式性的表演,不是垄断在少数人那里的艺术,而是一种使人获得其身份认同和自身主体性的那一系列实践。她用到了雷蒙・威廉斯的“情感结构”(structures of feeling)的概念,这显然是恰当的。对于雷蒙・威廉斯而言,资本主义世界的组织和统治,离不开文化,离不开个体对于社会结构的体认,也离不开以文化为中介的情感体验。相应的,一个群体要获得主体意识,实现团结,也离不开文化过程。这一点,在E.P.汤普森著名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得到过细致而深入的体现。在理论上,劳动者的主体性问题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它是很多理论家讨论的重心。简单举例,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就建立在对文化阶级性的讨论之上,阿尔都塞的“询唤”(interpellation)概念则强调了国家机器在主体生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福柯的“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和“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等概念则力图强调这一过程在微观层面上更为复杂的互动过程。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时代。正如哈特(Michael Hart)和奈格瑞(Antonio Negri)在《大同世界》(Common Wealth)中所论述过的,当前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通过图像、媒体、符号、感受、知识等中介,转向了对于主体性的直接生产[1]。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劳动者的主体性的塑造能够更加容易。恰恰相反,晚期资本主义生产的主体,往往不再是劳动的主体,而是消费的主体;是个人主义的主体,而非集体主义的主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会看到劳动者们羞于谈论自己的劳动,不愿意和“工人”这样的社会身份沾边。我们会发现,情调、欲望和消费占据了社会价值的核心,成为美好体验和意义感的主要来源,而这些体验往往是与劳动过程彻底分离的。这就意味着,一方面,面对晚期资本主义的世界,劳动者共同体意识的觉醒、共同命运的体认,变得异常困难。一方面,主体性问题也恰恰因此变得越发重要。我们想象未来世界的可能性,促进未来世界的可能性,恐怕更是要从主体性和文化问题入手。这一过程是身份政治的必需,也是另类现代性路径的希望所在。这一点,不仅对于阶级身份成立,对于性别身份、族群身份等其他社会类别,恐怕也同样成立。
吕途的书恰恰以一种质朴的方式为我们呈现了当今中国新工人群体主体意识形成的困难。在劳动场域,吕途非常敏感地提出了新工人群体的“过客心态”。过客心态,不仅是对自己劳动地点的否认,更是对自己劳动者身份的逃避。这种逃避,也带来了新工人们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和无奈。吕途和我们都面对这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三亿人的劳动者群体,会逃避自己的身份,会难以建立团结意识,而感到迷茫和没有出路呢?吕途给出的答案,实际上回到了马克思,即资本对于人的异化(虽然吕途自己很少提到这个概念)。这个答案显然没有错。然而,要进一步展现这一过程,这可能要回到对于中国的新工人所面临的历史境况。具体来说,这一个历史境况,可能有三个基本层面。
其一,我们所面对的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既不是马克思看到的资本主义发生早期的原始积累阶段,也不是成熟资本主义时期的福特主义阶段。我们面对的,是灵活劳动、灵活生产和灵活消费的资本主义。无论用“后福特主义”来指涉这一时期,还是用“新自由主义”来描绘这一阶段,这一时期的劳动和资本的组织形态,已经发生了重大变革。这一点在吕途的叙述中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吕途的调查说明,大量的劳动者,长期频繁地更换工作,无法获得一个稳定的职业生涯。大量的妇女,穿梭在家庭和工作的抉择之间,往往因为婚姻和家庭的需要而选择短期工种,成为更加流动和灵活的劳动力。劳动者的工作选择貌似丰富,而实际却越来越可以替代,越来越缺少稳定性和安全感。新工人群体只能依靠“灵活劳动”,在劳动力市场中寻求并且不断变换自己的位置。
其二,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的转变,在政治领域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点,汪晖在为吕途第一本书《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的序言中已经做了非常精练而且精确的总结。他非常正确地指出:“不是新工人群体缺乏阶级意识,而是产生这种阶级意识的政治过程终止了、推动这种阶级意识形成的政治力量转型了。”[2]在政治领域,传统的政党政治面临着汪晖所说的“代表性危机”,工人群体的斗争,在今天已经被限定在法律的框架内。政治领域的重组,使得新工人群体的斗争,缺乏曾经的组织结构。这也是一个全球范围内普遍发生的变化。不仅如此,NGO等新的组织模式的兴起,也标志着以工会为基础的团结也日渐衰落。而以NGO为主要团结方式的抗争,也更多地围绕着中产阶级的权利,不再以工人乃至劳动者的身份政治为中心。
其三,中国新工人群体还面临着自己的特殊问题,特别是户口制度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上述制度设计,使得他们至今仍旧没有完成自己的“离土”过程,一方面,他们在城市寻求工作机会;另一方面,作为保障的土地还留在农村,福利还留在户口所在地,无法跟随他们进城。他们的精神和肉体都始终徘徊在城乡之间。这也就是潘毅论述过的“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在潘毅看来,中国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是特殊的,城乡分割的制度,实际上有利于劳动剩余价值的最大榨取,也使得无产阶级化过程异常漫长。按照潘毅的判断,“作为一个劳动主体,他们始终是残缺的,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3]这一点,吕途在这本书里面也有所涉及。她用了很大的篇幅写了王福维的房子和王福维的购房抉择,在吕途看来,王福伟的购房行为是荒谬的,因为他其实根本不会去居住那个花费了他几乎全部积蓄的房子。但这个故事却深刻地反映出了中国新工人群体在劳动力再生产环节的困境。总体上看,中国的制度安排,在生产环节之外的劳动力再生产环节,进一步增加了新工人群体的流动性。面对土地、故乡、户口、城市,这一群体的挣扎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所谓新工人群体自身,变成了一个政治隐喻。
综上所述,中国的新工人群体,面临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世界在全球范围内生产方式的激烈重组,政治制度的整体变革,也面临着中国内部现代化道路的制度壁垒。这些不同的侧面,都在吕途的写作中,得到了细致的呈现。她的叙述让我们看到,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廉价劳动力闻名的地方,劳动者群体的精神状态是怎样的,如何被塑造的,她们/他们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认同又是如何被消磨的。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讲述的包括王佳和程永芳的女性故事,吕途也让我们看到,主体性塑造的过程,不仅蕴藏了阶级政治,也包含着性别政治、代际政治等一系列范畴。
作为一个研究者,我也关注吕途书写的新工人群体,也曾经在吕途长期生活的村子生活过几个月。根据我的体会,对新工人群体的研究,实际上还有很多可以推进的地方。譬如,新工人群体的界定,可能就需要概念上的廓清。如果说,新工人群体,就是户口在农村,而生活地点在城市的劳动者们,那么,这个群体的界定,事实上并不是依据他们和资本的关系,或他们的劳动内容,而是依据他们和国家的契约,依据他们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公民权来确定的。在与国家的关系方面,这一群体基本是同质的,但是就劳动层面而言,他们内部的分化就特别复杂。工厂工人、小企业业主、摊主、企业雇员、外地高校毕业生,这些人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被囊括在新工人群体中。以市场为中介,新工人群体中的很多人已经成为能人、民间资本家、私企业主。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历史过程,如何理解他们之间的分化乃至冲突。此外,作为研究者,除了面临上述新工人群体的分化问题,我们也面临着“整合”的问题,即如何把中国新老工人的处境和变迁纳入一个共同的分析框架之中,如何理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团结。
正如我在文章开头提到的,“新工人”是一个未完成的概念,一个开放的概念。未来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群体的自我意识的确立和身份政治的有效事件。吕途的著作,本身也就是探索的一部分。而这种探索的力量,不仅包括吕途这样的知识分子,也包括其他的力量。譬如,近些年国家已经在福利制度上做出了很多变革,新农合的推广、城乡一体化的推进、新居民的政策、户口制度即将面临的大范围的调整,都对这个群体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策略存在影响。而与此同时,从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到2010年以来的富士康事件,再到2014年7月哥式比女工周建容的自杀事件,这些事件充分说明,新工人群体对于权利和尊严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而这些貌似单一的历史时刻,也许会在工友摸索自身主体性的历史进程中成为重要的节点。
注释
[1]参见Har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09, Common Weal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汪晖:《我有自己的名字》,载《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3]潘毅:《农民工――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6期。
作者单位: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人类学系
Articles are uploaded by users and are for non-commercial browsing only. Posted by: Lomu, please indicate the source: https://www.daogebangong.com/en/articles/detail/pycsi903h0xc.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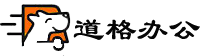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196条)
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