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西方学术界对民族主义问题的持久研究兴趣缘于民族主义对近现代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的直接影响,也因为民族主义具有既对人类的安全、公正等最深层的迫切要求作出积极回应,又引起世界性的动荡和人类之间的大规模兵戎相见的两面性。在对民族主义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方面,西方学术界显然走在了前面,但国内学术界对之的了解和研究似乎并不很透彻。西方学术界对民族主义的研究可以分为19世纪、19世纪末至20世纪50年代和自20世纪60年代延续至今天的三个阶段。当西方的民族主义研究进入第三阶段之后,各种不同的民族、民族主义理论应运而生,这对依然在当今的国际社会有着重大影响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民族主义 西方学术界 民族主义研究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6)04000108
作者简介
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关系系主任。曾先后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美国新泽西拉马坡学院、英国剑桥大学、卢森堡欧洲与国际事务研究所、日本京都立命馆大学作访问研究和访问讲学,为剑桥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访问研究员。著有《解读美欧: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美欧关系》和《大变局:全球化、冷战与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等学术专著,并在中外学术刊物上数十篇。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产生于18世纪西欧和北美“为某一群体争取和维护自治、统一和认同的意识形态运动”,[1]在经历了跨越四个世纪的自身历史发展和对近现代的人类历史发生巨大作用之后,至今依然对进入新千年不久的人类社会具有丝毫不能令人忽视的影响。正是因为如此,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不论中外,尤其在西方,始终是社会科学界,包括国际关系学在内的学术研究重点,更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有关民族主义的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呈日趋上升的势头。由于当代西方民族主义研究的兴盛既有现实国际政治的原因也是有其学术史渊源,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此作一些研究和分析。
一
西方学术界对民族主义问题的持久研究兴趣,以及近年来西方更趋高涨的相关研究热情主要出自下述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民族主义从其产生初期直至今天始终伴随着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和变化。记录显示,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这一词汇最早被使用于18世纪末期, 当时德国哲学家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 和法国反对革命的神父奥古斯丁・德・巴鲁尔(Abbé Augustin De Barruel)使用了该词并使之具有可辨识的社会和政治的含义。[2]从此之后,民族主义这一词汇伴随着民族主义思想意识形态的全球性传播,以及民族主义运动的世界性扩展,自始至终见证着18世纪后期以降人类的两百多年,却已经跨越了四个世纪的世界历史。可以这么说,如果不了解民族主义这一词汇,不了解民族主义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及其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就根本无法全面地了解这跨越四个世纪的近代、现代乃至当代的国际关系史和人类历史本身。也正是因为如此,民族主义一旦在西方兴起,对其的学术研究也随之产生,并且随着民族主义的发展而发展,而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国际关系学家们则在西方的民族主义研究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第二,民族主义对近代西欧、北美各国的兴盛崛起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民族主义诞生于西欧和北美,之后便通过强调个人的民族认同或民族身份以及民族与国家结合,逐渐成为西欧和北美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对现实的认知乃至道德的组织形式,并由此而成为构成社会一体化的基础。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推动建立和建构民族国家,并且在民族国家的政治架构中体现其包容性、确立所有的社会成员享有基本平等的权利和自治的核心原则。这样的民族主义原则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赋予具有民族认同感的大众个体以一种尊严感,促使大众个体不仅确立起自己的民族认同或身份,并将自己的民族认同上升至国家认同,乃至使自己成为民族国家的主人。在民族主义激励下所产生的这种曾未有过的尊严感从一开始就构成了近代以来民族爱国主义和对民族事业忠诚的基础,而这一切恰恰首先发生在西欧和北美,并且对近代西欧和北美的崛起产生直接的影响。有西方学者认为,正是民族主义构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精髓。“‘资本主义精神’是民族主义固有的集体竞争意识的经济表象――而民族主义本身是民族国家成员对国家尊严或威望的情感投入的产物。”[3]于是,近代西欧各国以及美国均因强烈的民族情感而激发出充分的经济活力,以致它们的经济竞争力能不断地提升而形成崛起之势。对于具有如此能量的民族主义,西方学术界自然会始终如一地重视研究,就像韦伯及其后继者重视研究新教伦理一样。
第三,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对亚非拉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以及新独立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随着西方的崛起和扩张,亚非拉地区渐次地陷入被西方殖民化的过程,不公平的世界由此而形成。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方列强在向全世界实行殖民扩张的同时,却在“不经意”间将源自于西方的民族主义传播到了广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正如史密斯所言,“民族主义常常对处于不公平世界大多数人民所感受到的社会剥夺和压迫做出响应。”[4]亚非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正是运用来自于西方宗主国的民族主义思想意识形态,结合自身的历史、文化认同,强调在一个安全的国家内人们有自己的民族和文化的权利,要运用暴力的或非暴力的手段来争取摆脱殖民统治的外部强权,完成民族建构和建立自己民族独立的国家。民族主义还十分有力地帮助争取独立的人民将集体的记忆与特定的祖先领土联系起来形成祖国的观念,并且通过民族建构而自然地团结人民。这对整个世界形成民族国家的国际政治体系是至关重要的。就如民族主义早期在西欧、北美曾经做过的那样,二战后,亚非拉地区的各种民族主义也在推动建构“自己的民族”、促进个体以“记忆的领土化”方式将自己定位在民族国家的时空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此外,民族主义也同样赋予亚非拉各国人民独特的认同和尊严,促使它们赢得国家独立后在经济建设中勇往直前。然而,民族主义为何能在其发源地之外的世界各地同样产生如此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则成为西方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问题。对民族主义的持久、深入的研究也就很自然地处在情理之中。
最后,民族主义在允许全世界的大小群体进入国际政治舞台,回应人们的安全、公正和认同等普遍要求的同时,也常常会导致持续的民族、族群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国际冲突。这些冲突紧紧地伴随民族主义的发展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跨越四个世纪的国际紧张、危机和战争,也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独立国家的内战。从民族主义在西欧和北美诞生之初,这一前无古人的意识形态和运动就不断地加剧当时以西欧为中心的国际政治体系中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性和冲突性。由于民族主义强调的个人从属于民族而民族单位应该与政治单位(国家)对等的政治理念,且民族则是全体公民的集称,他们拥有的权力使他们与国家利害相关,因此,在民族主义推动下所产生的民族国家内的公民总是具有强烈的“我们的”国家自然会比“他们的”国家好的爱国主义民族情感。[5]在这样的民族主义情感作用下,首先产生于西欧和北美的民族国家内的公民们从一开始就具有的强烈排外情绪。于是,在民族主义作用下所产生的公民意识中的“我们”与“他们”的情感就会在激发本国经济活力的同时,推动与他国的激烈竞争,而这样的竞争在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之间表现得更为突出,其中德国崛起之后所产生英德之间的激烈竞争就是最为明显的例证。不仅如此,民族主义还经常会激发出强烈的民粹意识,而这种民粹意识很难和民族意识或沙文主义式的爱国情操区别开来,[6]“我们的”国家不仅要比“他们的”国家好,而且要比“他们的”国家强,如果“他们的”国家要比“我们的”国家强,“我们”就应该消灭“他们”。于是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之下,从西欧产生的民族国家国际政治体系始终充满着激烈的、具有浓烈民族斗争色彩的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世界近代史上的英法战争、拿破仑战争、普法战争、克里米亚战争等无一不是这一类型,在很大的程度上,一战和二战也与民族主义在这方面的作用相关联。更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一系列的国际战争一步一步地向总体战(general war)的方向演变,因为通过求助于民族主义,各民族国家终于有能力动员全体人民来保卫祖国乃至推进侵略扩张。战争的规模随之不断扩大,战争中的军队、平民和前方、后方之间的界线由此而不断地模糊,以致最终导致不分军民和前后方的、具有肆意屠杀性质的总体战争。
在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随着欧美的全球性扩张而向全世界扩散的过程中,世界性的民族主义运动也不断地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根据国内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整个20世纪全世界就经历了三次民族主义浪潮。[7]毫无疑问,所有的这一系列民族主义浪潮都是处于不公平世界大多数人民对所感受到的社会剥夺和压迫做出反应的结果。但是,在这三次世界性的民族主义浪潮中,民族主义不仅推动着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反抗和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且同时也给世界带来了巨大动荡、冲突乃至战争。比如在一战前后所产生的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性民族主义运动致使东欧地区出现一系列新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些新的民族独立国家在回应本国主体民族的独立、安全、公正等要求的同时,却给中东欧地区的国际关系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也给这些国家内部民族关系留下很大的隐患,这些不稳定和隐患无疑与二战的爆发不无关联。在二战后的20世纪第二次民族主义浪潮中,也不同程度地产生了类似的情况,民族主义在促进亚非拉民族解放的同时,令人遗憾地也成为亚非拉区域冲突和内战的渊薮。不容否认,在第二次民族主义浪潮过后所产生的南亚印、巴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乃至战争,中东地区巴以之间的延绵不绝的冲突和战争都与民族主义关系密切。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也不能例外地对世界的稳定形成巨大的冲击。自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之后,在民族主义的巨大冲击之下,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拉伐克在1991、1992和1993年相继解体,20多个新的民族国家由此形成。与此同时,在巴尔干、车臣、库尔德、爱尔兰、魁北克、巴斯克以及亚非其它地区为民族主义理想而进行的斗争此起彼伏、延绵不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这又一次的民族主义浪潮导致了世纪之交的一系列战争:海湾战争、波黑战争、车臣战争以及北约对南斯拉夫的战争等。
民族主义的这种两面性的特征,即既对人类的安全、公正等最深层的迫切要求作出积极回应,又引起世界性的动荡和人类之间的大规模兵戎相见,必然强烈地刺激全世界的学者对之进行持久和系统的研究,因为只有通过对民族主义全面系统的研究才能帮助人们深入领会民族主义在现代世界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才能引导人们系统地理解民族主义这一不断地鼓动全世界人民,同时又令全世界人民感到困惑,但却始终是和人类命运生死攸关的和变化多端的力量。
二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民族主义的研究成果颇丰,极大地拓展了研究视野,繁荣了学术园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学术界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似乎不很注意对西方相关研究做系统的研究和介绍。尽管近年来已经有相当多的西方民族主义理论专著被译介到了国内,但国内学者对这些译著做系统的梳理工作则很不够,而对西方学术界有关民族主义研究的流变做全面的考察和分析则更显不足。可能是出于上述的原因,总体而言,国内学术界对西方学术界有关民族主义研究的历史演变乃至现状的认识不很充分,其具体的表现如次:
1.对民族主义在西方形成之初的思想背景以及在其形成后初期的19世纪西方学术界对之的理论考察则尚未为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其别是对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是否与同样也是意识形态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一样,拥有其自身的大思想家这一引起西方学术界极大争议的课题没有做必要的研究与考察。须知,在很大的程度上,对上述这方面的学术探索和研究十分有助于我们理解民族主义的发生、发展及其对当今国际社会的影响,同时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当代西方学术界有关民族和民族主义研究的各种理论流派及它们之间的学术争论。[8]
2.对不同时期西方学术界研究民族主义的重点不甚了解。比如对一战后的20年代至二战后的50年代一系列西方著名史学家,如卡尔顿・海斯(Carlton Hayes)、汉斯・科恩(Hans Kohn)、E・H・卡尔(E. H. Carr)、路易斯・斯奈德(Louis Snyder)等所进行的民族主义问题研究的重点不是很清楚。国内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是探讨了西方民族主义的思想渊源、历史背景、形成过程、传播方式等,抹去了民族主义宣传家加在这一问题上的神话色彩,并为后来研究这积累了大量资料。”[9]虽然,这样的分析不能算错,但没有点出该时期西方民族主义研究的真正重点――对民族主义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分类研究。史密斯指出:“到20世纪20年代,卡尔顿・海斯和汉斯・科恩开始了他们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谨慎剖析,并且试图将民族主义的不同样式整理为明确的和重现的类型。海斯的著作可能是首次采纳了更为中立的立场,一种寻求区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各种流变的立场。”[10]正是因为对该时期西方民族主义研究的重点不熟悉,所以竟然在进入21世纪之后,国内还有学者认为,“在国内外关于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中,众多学者……未对‘民族主义’概念进行科学分类”,[11]而没有认知到“有关民族主义的分类问题恰恰是西方学术界对民族主义研究的重点之一”。[12]
3.对西方学术界在民族主义研究中的理论体系认识不清,对西方学术界所用的相关术语也时有误解。由于国内学术界长期缺乏对西方民族主义研究的发生、发展、演变以及相关成果作系统的研究分析,因此有的国内学者在接触了一些西方的相关研究成果之后便不加细究地介绍和引用,以致产生相当程度的误导。比如有学者将当代西方相当有影响的研究民族(nation)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原生主义理论(Primordialism)、现代主义理论(Modernism)和族群-象征主义理论(Ethno-symbolism)误作为研究族群(ethnicity)的理论,并且把美国学者本尼迪特・安德森(Benidict Anderson)阐释“民族”(nation)时所用的专门术语“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误释为是对“族群”(ethnic group)的分析。[13]类似的误解为数不少,其原因可能与国内学术界对英语术语nation、nationality、ethnic group、ethnicity的汉译不一致有关系,但是,缺乏对西方民族和民族主义理论的系统、深入研究可能也是比较重要的因素。
4.对西方学术界有关民族主义研究的成果没有深入的考察和借鉴导致国内学术界对民族主义某些认识上的误区。我们似乎可以通过考察和比较分析内地几部重要的工具――1979年出版的《辞海》、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以及2000年出版的《辞海》对民族主义的不同释义来说明这方面的问题。1979年版《辞海》对“民族主义”的释义为:“资产阶级对于民族的看法及其处理民族问题的纲领和原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起着不同的作用。”1986年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的释义则为:“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是他们观察、处理民族自问题的指导原则、纲领和政策。”而2000年版《辞海》对1979年版《辞海》的“民族主义”释义作了比较大的修改,其前三句话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处理民族问题、民族关系的原则、纲领和政策。早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以前就已存在。至资本主义时展为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故亦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毫无疑问,这三种对民族主义的释义在一定的程度上代表着我国学术界对民族主义认识的演进,但是,其相同之处在于都强调民族主义的阶级性,只是渐次地将原先认为的资产阶级属性扩展为地主、资产阶级乃至小资产阶级的属性。然而,恰恰是这种对民族主义解释的变化反映出国内学术界对民族主义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其中包括缺乏对西方民族主义研究成果的全面考察和分析。
一般而言,西方学术界在民族主义缘起于西方这一基本看法上是有共识的,而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此观点持相同的认识也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西方学术界也比较一致地认为民族主义的产生是与西方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相关联。因此,民族主义缘起的西方性和现代性几乎是西方学术界的某种常识,并且基本上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分析相一致。然而,从《辞海》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相关释义中可以看出,国内学术界对这些基本的学术观点没有正确的把握。如果说《辞海》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在强调民族主义的阶级性方面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还有些一致的话(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从来没有认为民族主义还有地主阶级的属性),那么在阐释民族主义缘起的西方性和现代性方面则远远地背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而恰恰在这两点上,西方学术界经过长期的研究则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关分析得出近乎一致的结论。国内权威辞书对民族主义的如此阐释或许是导致国内学术界对民族主义的认识偏差的重要原因。有学者甚至提出:“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忠君没有爱国,只有民族主义没有爱国主义。”[14]如果国内学术界能对西方学术界关于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并且了解到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所强调的民族主义缘起的现代性和西方性迄今依然具有说服力的话,那么就不会提出这种看上去很新颖却既否定了民族主义缘起的西方性也否定了民族主义的现代性的观点了。
从上述四个方面的分析可见,全面系统地了解、分析和研究西方民族主义研究的各项成果是十分重要的,否则会给国内有关民族主义的学术研究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并不利于我们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和把握。然而,在我们全面深入剖析西方民族主义研究的成败得失之前,似乎还应该对西方民族主义研究的整体历史流变有一个大体的分析。
三
在有关西方民族主义研究的历史流变问题上,国内有学者认为,西方学术界对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开始于一战之后,并强调,“从那时起,民族主义研究始终与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浪潮联系在一起”。[15]根据这样的看法,西方有关民族主义的学术研究可以分为三次高潮,即一战之后到二战后初期的因民族主义引起两次世界大战而产生的研究高潮、二战后的60年代到80年代由二战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和非殖民化而导致的研究高潮,以及20世纪90年代由苏联集团和第三世界各地喷涌而出的民族主义运动引起的又一次研究高潮。[16]有些西方学者也持有类似的看法,他们认为:“尽管民族主义一直有普遍深入的影响,但是直到相对较晚的社会科学家们才对之认真研究。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和20世纪早期,民族主义被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们视为仅仅只是一匆匆过客,由此也不被看作是‘智力的学术问题’。”[17]当然,西方学者并没有由此而认为西方学术界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与20世纪的三次民族主义高潮存在着关联。
虽然,强调直到一战之后西方社会科学家才开始对民族主义进行全面认真的研究有事实基础,因为西方社会科学家全面系统地对民族主义进行研究确实形成较晚,甚至可以说是在二战之后,但是,上述提法似乎也有不太全面的一面,即忽视了一战之前西方学术界实际上早已开始了对民族主义研究这一事实。尽管西方学术界早期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主要由历史学家们来展开,但这并不意味着相关的研究就不是学术研究,他们对民族主义的研究工作给后来的社会科学家们,其中包括国际关系学者们以很多有益的启示。更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0世纪之后,在一战爆发之前,随着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以及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两位西方社会学奠基人也对民族主义展开研究之后,西方学术界的民族主义研究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民族主义问题开始成为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不能否认,韦伯和涂尔干的相关研究并不十分系统,但是他们对民族主义问题的一系列论述却对整个西方民族主义的研究,尤其对当代西方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理论的建构产生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将西方民族主义的研究分成与20世纪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相对应的三次高潮虽然也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如果深入地考察一下,则会发现与实际并不十分相合。其实,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之后,尽管随着新一轮的民族主义高涨,西方学术界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也出现过热潮,但是就具体的民族主义理论流派和理论交锋而言则依然是60年代以来西方相关研究的延续。
实际上西方学术界对民族主义的研究应该起始于19世纪,其中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研究。在相当的程度上19世纪可以被视为西方民族主义研究史上的第一时期。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直到二战之后的20世纪50年代是西方民族主义研究史上的第二个时期,该时期是西方民族主义研究的逐渐深入阶段,经过一战前马克斯・韦伯和涂尔干相关研究的过渡,到一次大战后以民族主义分类学为主导的西方民族主义研究产生了一系列很有影响的学术成果,直至今天依然对我们认识民族主义有很大的影响。从二战后的20世纪6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是西方民族主义研究史上的第三个时期。不可否认的是,该时期西方学术界对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最为广泛、深入、全面和系统。一系列相关的民族和民族主义理论在这一时期被建构了起来,不同的学术流派从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方法全方位地阐释民族和民族主义现象,为人类更为深入地理解民族主义这一不断地影响和塑造自己行为的全球性思想意识形态和运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世纪是民族主义在西方全面扩展的世纪,也是西方学者对民族主义展开研究的第一个阶段。毫无疑问,该阶段是西方民族主义研究的初级阶段,因为尽管当时因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尤其是因后者,民族主义迅速地在欧美传播,并且十分有力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但是对民族主义的研究却并没有很快形成西方学术研究的重点,不过,不少西方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们实际上已经开始注意对民族主义进行研究和讨论,如朱莱・米歇莱(Jules Michelet)、爱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海因里希・冯・特里茨科(Heinrich von Treischke)、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厄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乃至马克思和恩格斯等都在他们的著作中对民族主义进行过某种探讨。不可否认,这些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们的主旨在于弘扬他们自己的理论体系和主义而不是深入研究民族主义,因此他们对民族主义所作的讨论很多都带有比较强烈的价值判断或批判色彩,因此而显得不是十分客观深入,同时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也缺乏系统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一系列相关研究成果却对后世的民族主义问题学术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民族主义的阶级分析直到今天依然具有很大的学术影响。
从19世纪末开始到20世纪的50年代,随着马克斯・韦伯和埃米尔・涂尔干介入到卡尔顿・海斯、汉斯・科恩、E・H・卡尔等著名学者对民族主义的分类研究,西方民族主义研究进入第二个时期,该时期是西方民族主义研究比较深入的时期。虽然韦伯和涂尔干与19世纪的思想大师们一样,并不将研究民族主义作为构建自己理论体系的主要工作,但是他们的研究却是从一个比较系统的社会学角度切入,因此对促进民族主义问题研究的深入很有影响。当代西方各种民族主义理论的建构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韦伯和涂尔干对民族主义的某些经典性阐释的影响。从历史的观点看,到20世纪20年代,卡尔顿・海斯和汉斯・科恩开始了他们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谨慎剖析,并且试图将民族主义的不同样式整理为明确的和重现的类型,即对民族主义做系统的分类。[18]不仅如此,海斯和科恩等学者的民族主义分类研究确实让我们感觉到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复杂性。这样的分类还在其分析论述的深层次层面揭示过民族主义的首个完整的历史道德分期。[19]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直到二战之后的60年代,即西方的民族主义研究进入第三阶段之后,西方学术界才在世界性的非殖民化和亚非新兴民族国家不断涌现的大背景下开始将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问题进行立场中立的且系统、深入和全面的专题研究。随着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不断发展以及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各种不同的民族、民族主义理论和相关的学术争论应运而生,相关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概而论之,当代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主要可以分为:“原生主义”(Primordialism)、“永存主义”(Perennialism)、“现代主义”(Modernism)、“族群-象征主义”(Ethno-symbolism)和“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等几种。迄今为止,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现代主义”和“族群-象征主义”。虽然“后现代主义”民族理论在总体理论架构上与前几种理论迥然不同,即前者是构建,而后者是解构现代社会,以致它的学术影响力渐增。但是“后现代主义”民族主义理论似乎还在发展的过程中,并且因其自身的分散性而很难迅速成为主导的理论范式。然而,不论怎样,本阶段的西方民族主义研究迄今依然在延续,而所有的这一系列的民族主义理论也还都在不断的充实和发展过程乃至争论中,在不断地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和确定现代世界的面貌方面,没有哪个政治学说能比民族主义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20]
纵观西方民族主义研究的发展历史,西方学术界对民族主义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这些成果对人类认识依然在当今的国际社会发生重大影响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运动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目前我国在不断地融入整个世界体系、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全面地推进和谐世界建设的过程中,深入地认识迄今依然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各式各样的民族主义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不言而喻,在西方民族主义研究历史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成果以及各种理论范式,无疑都为我们提供了认识民族主义的有效工具。常言道,“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果西方关于民族主义研究的成果和理论是我们认识民族主义的有效工具或器具之一,那么,我们就需要对之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的目的就是在这方面能起某种抛砖引玉的作用。
注释:
[1][英]安东尼・D・史密斯:《民族主义》,叶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1页。
[2]史密斯:《民族主义》,第6页。
[3][美]L ・格林菲尔德:《资本主义的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张京生、刘新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28页。
[4]史密斯:《民族主义》中文版序言。
[5]有关的民族主义所产生的“我们的国家”或“我的国家”与别人的国家之间关系的具体讨论参见[英]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105页。
[6]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第105页。
[7]郝时远:“20世纪三次民族主义浪潮评析”,载《世界民族》1996年第3期,第3-9页。
[8]有关民族主义是否拥有自己的大思想家,笔者在“西方民族主义兴起的思想背景”(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12-18页)一文中对此作了某些讨论。
[9]徐波、陈林:“全球化、现代化与民族主义:现实与悖论――《民族主义研究学术译丛》序言”,载[英]埃里・凯杜里:《民族主义》,张明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10]A. D. Smith, Myths and Memories of the 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36.
[11]金鑫、徐晓萍:“有关民族主义的几种类型”,载《欧洲》2002年第1期,第98页。
[12]Umutzkirimli,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Ltd., 2000, p.57.
[13]纳日碧力戈:《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云南教育出版社,第44-66页。
[14]叶文宪:“中国古代有没有爱国主义――论国家与王朝、爱国与忠君、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区别”,载《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1期。
[15]徐波、陈林:“全球化、现代化与民族主义:现实与悖论”,载凯杜里:《民族主义》,第21页。
[16]同上,第21-22页。
[17]kirimli,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p 1.
[18]A. D. Smith, Myths and Memories of the 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40.
[19]Carlton Hay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Modern Nationalism, New York: Smith, 1931;A.D. Smith,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London: Duckworth, 1971, ch. 8.
[20]kirimli,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p.1.
Articles are uploaded by users and are for non-commercial browsing only. Posted by: Lomu, please indicate the source: https://www.daogebangong.com/en/articles/detail/ptu2dh004kza.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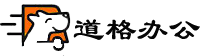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196条)
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