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中探讨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体系。就要坚持我国在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中的话语权和自。党中央国务院对民族概念的新阐释,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概念的理论在中国化过程中的具体实践,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促进中国民族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理论;民族概念;话语权
[作者]黄仲盈,广西民族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南宁,530028
[中图分类号]A811,D0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2-0019-006
2005年5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中央领导对“民族”概念做了新的阐释:“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说来,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一阐释至少说明“民族”具有以下两个基本性质特征:一是具有历史性,是历史的产物。“要给‘没有历史的民族’找一个范例,是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除非在乌托邦中寻找),因为所有的民族都是有历史的民族”,“祖国、民族――这是历史的范畴”,“民族不是种族的共同体,也不是部落的共同体,而是历史上形成的人们的共同体”,“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等等,以上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定义的表述,虽然内容不尽相同,但都强调了一点,那就是:民族是历史的范畴,是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二是具有生态性,是不断传承和发展的。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心理认同等方面的共同性,实际上就是这些因素在民族交往和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相互交流、吸收、分化、融合的一种再生传承过程,在重组的生态延续中逐渐沉淀为内在的稳定性。
中央领导对“民族”概念的新阐释,通过列举特征的表述方式,既吸收了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合理成分和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又充分考虑到中国乃至世界上各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实际,科学、准确地阐释了民族这个共同体的内涵,“是迄今为止关于民族内涵最为科学的阐述,具有科学的严谨性和普遍的适用性。”龚永辉教授也从话语权、学理性、国家安全理念等方面,“由衷推崇”民族概念的这种新阐释,认为党中央国务院总结的民族概念,“根植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涵盖了中华本土与世界各地多形态、多层面族体的基本特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概念的理论在中国化过程中得到了必要的扩展和完善。”
一、民族概念话语权与中国民族理论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中国民族理论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其中,民族概念在我国的发展轨迹就是一个典型。民族概念在我国的发展过程中,能够坚持中国的“特点”和“特性”的内容阐释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引进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
综合各种史料,在斯大林民族概念引进我国的前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虽然在很多著述和文章中大量运用了民族一词,但并没有针对民族这一社会现象进行必要的阐释,斯大林民族概念作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的一个经典概念,其构成民族定义的“四要素统一”的原则,对当时我国的政坛和理论界都具有很大的权威性,这在早期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民族政策中就有所体现。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就曾经效仿苏联,提出了联邦制建国的设想,这在一系列的政策中都可以看得出来,如“二大宣言”提出了“共和国”的建国方案,“统一中国本部”,“蒙古、、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立民主自治邦”;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也规定,各少数民族有权“同中国脱离,成立独立国家”,也有权“加入中国苏维埃联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同时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决议案》中同样重申了《宪法大纲》中少数民族有权决定“成立独立国家”、“参加中国苏维埃联邦”、“在苏维埃联邦内成立自治区域”等三种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前苏联之所以成立联邦制的国家,是由当时俄国的历史和政治环境决定的,一方面,在十月革命以前,俄国的各少数民族都有较为单一的聚居地,经济、文化、语言、生活方式等都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各民族时间的区分比较明晰;另一方面,早在俄国形成统一的国家之前,多数的非俄罗斯民族都建立起了自己独立的国家政权,各民族之间依存性弱,独立性强。应该说,俄国的这种民族分布状况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斯大林民族定义产生的历史和现实基础。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制定民族政策时,规定少数民族有权“成立自己的独立国家”,从中就可以看出斯大林民族概念中的语言、地域、经济生活等要素在这里显示出了其对早期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影响。但是,我国并不是一味地遵从和效仿前苏联,如规定各少数民族在苏维埃联邦内“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的政策就表明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注意到了我国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错居杂处的分布格局,在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上开始有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的探索倾向。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建立健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在民族识别的过程中,根据我国的历史与现实情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了“名从主人”的民族识别原则,不再一味遵循斯大林的民族概念,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早期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遵循的“中国的具体环境”、“中国的特点”、“中国的特性”的原则,实事求是对我国各民族进行识别和划分。1957年3月25日,在筹建广西壮族自治区问题座谈会上提出的“在我国,不能死套斯大林的民族定义”的话语不仅是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质疑,更重要的是强调了民族识别必须遵循中国的社会现实。1970年12月18日,在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谈到关于民族的类分时指出:“什么是民族啊?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上层,剥削阶级,少数;这一部分可以讲话,组织政府,但是不能打仗、耕田、在工厂做工。90%以上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没有这些人就不能组成民族。”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主要还是从阶级的观点来分析民族现象,但是,这已经“特别关注民族内部的差异性、民族成分中的人民主体性,与斯大林民族定义的视角和思路都绝然不同。”至此,我国在坚持民族概念话语权上已经是显山露水了,对斯大林民族概念由最初的遵循走上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发展道路,民族理论中的“中国特点”和“中国特性”等元素也日趋突出,从而也使得众多专家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就呼吁必须建立中国自己的民族理论体系,并指出“这种理论体系,不是马列主义之外的什么别的体系。而是马列主义的中国化”。
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国著名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
论,该理论既体现与斯大林民族概念完全不同的、崭新的民族学研究与探索之路,又符合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近代以来,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提出以前,在民族现象的理解和阐释上,都是以西方的划分标准为基本出发点。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的民族学理论曾长期占据我国民族学界的主要阵地,特别是斯大林的民族概念更是一度成为了民族识别的理论依据,虽然后来有所质疑,有所批判,甚至也遵循了“名从主人”的识别原则,但是,这只是一种政策上的“软抵制”,斯大林的民族概念在我国理论界还是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以至于民族识别之后学术界对民族概念的争辩,很大程度上还只是针对斯大林民族概念的修修补补,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多元一体”理论的提出,完全抛弃了斯大林民族定义所圈定的框架,根据中国的民族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是“政治一体,文化多元”的集团格局,其从宏观的角度指出,民族不再是以各种要素相统一的人们共同体,而是“民族意识在社会关系的作用下形成了具体的认同体系”,而民族之间的区分标志则是“与这个认同体系相应的一切社会或者文化因素”。这就将“民族”从一个禁锢的“统一体”中释放出来,不仅更能体现出民族的本质特征,同时符合我国的历史实际,“为我们认识中国民族和文化的总特点提供了一件有力的认识工具和理解全局的钥匙。”虽然,“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概念的阐释,只是针对于“中华民族”这一政治文化共同体的具体论述,缺少一种普世性民族的划分标准,但是,它毕竟从根本上突破了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民族这一人类历史现象的传统理解,从而为我国的民族学理论开辟了一条崭新的探索之路。
2005年5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国务院对民族概念进行了新的阐释,至此,长期影响我国民族理论界的斯大林民族概念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重新阐释下彻底解构了。“在一定的程度上突破了斯大林民族定义的模式,更加符合中国民族国情的状况。”应该说,党中央国务院对民族概念的新阐释,不仅第一次出现在党和国家的正式文件中,而且也是对我们党长期以来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政策的补充和完善,标志着中国民族理论话语权体系的建立和日趋完善。
二、构建中国民族理论学术话语体系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
民族概念作为民族理论的第一块基石,长期以来在概念的界定上纠缠不清,缘其原因,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内涵缺乏深刻的认识,或者说是陷入了一种机械的中国化当中,即习惯于用经典的概念来解释社会现实,用定义要素的框架来区分民族现象,以今人的观点去划分古代的人类群体,忽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所强调的“中国”元素。所以,要构建中国民族理论学术话语体系,体现在民族概念上,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中国”元素。所谓的“中国”元素,即“中国的具体环境”、“中国的特点”、“中国的特性”,主要指的是我国的传统文化,是指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创造的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从时间上讲,“它指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文化”,而这一时期,恰恰就是孕育我国原生态民族概念体系的过程。我国古代社会长达数千年,其社会结构主要是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宗法制度社会。因此,其中所蕴含的封建伦理性、教化思想、人文精神也使得我国的传统文化成为了世界上惟一一种长期延续发展、从未中断过的文化体系。这种状况体现在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上,就是我国古代“华夷之辨”和“华夷互化”的过程。历史上,中原文化无论是经历春秋以前“南夷”、“北狄”的入侵,战国至秦汉时期与北方少数民族的长期对峙,十六国时期的“五胡乱华”,还是宋元时期契丹、女真、蒙古人的南下,明末的清兵入关,始终都保持了一种包容的胸襟和强大的凝聚力,这种包容贯通的精神就是我国古代“大一统”思想的具体表现。在“大一统”思想中,“华夏”、“夷蛮”等称呼只是一种笼统的概念,在一定的条件下两者会发生“互化”现象,所谓的“华夏”与“夷蛮”之间的区别不只是等级身份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彼此生活、生产方式、风俗习惯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不同。有学者据此提出,我国古代所认为的民族共同体,“实际上是一种文明共同体。”这种观点是否已经成为定论尚且不提,但文化贯穿了我国古代各种族类发展的全过程却是不争的事实。长期以来我国“华夏”诸族与“夷蛮”之间发生的各种战争,最终胜利的不是军事的征服,而是落后的文明被先进的文明所同化,这正应了马克思曾经说过的话:“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在我国“大一统”和“天下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在征服与被征服的过程中,我国的传统文化体系并没有如一些国家那样容易发生断层,而是形成了一种和而不同的多元发展格局:一方面,各民族之间长期的交往、流动以及战乱使许多民族形成了一种大杂居、小聚居、错居杂处的分布局面,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和交融;另一方面,在这种相互交往和交融的过程中,血缘、地缘的关系逐渐模糊,维持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主要是以文化作为联系纽带,从而也使得民族有了一种延续再生的生态传承性,即是说,文化使民族的属性成为了一种可以后天变化的属性。这不仅是我国各民族发展的独特之处,还为后来我们考察千变万化的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时提供现实的基础。所以,对于我国古代的各种族类观,无论是郝时远所认为的是一种“地域性文化类型群体的概念”,还是王柯所指出的“实际上是一种文明共同体”,其中都注意到了文化在民族发展过程中的传承作用。鸦片战争以后,我国众多专家学者纷纷引进西方的民族理论,站在西方的立场上,以在西方文明发展中形成了民族概念理论对我国的民族现象进行条块分割,这种以一种文化来阐释另一种文化的现象,在学术上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由于背离了我国的传统文化,以至于在很长的时期内,我国在民族概念的界定上处于一种模糊、众说纷纭的争论当中,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提出,才重新引发了专家学者们对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思考。
2、应该深刻理解中国化中“化”的含义。“化”的对象主要是指西方的理论,至于如何“化”,李亦园就曾经指出:“不但要修正西方的理论以适应吾国的文化,而且应该更进一步创建我们的理论。”我国关于民族一词的运用,主要还是借鉴近代西方民族主义运动的成果。近代西方之所以需要“民族”一词,是因为资产主义生产发展的需要,是与民族国家相联系的。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客观需要新兴的资产阶级封建制度设置的种种障碍,建立起新兴的民族国家。而这种民族国家,西方提倡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模式,这种单一民族国家的模式在我国近代思想家和革命派中得到了推崇。早期孙中山在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时,就显露出了要建立由汉族统治的单一民族国家的倾向。这里,所谓的“中华”,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将其改造成为了专指“汉族”的狭义概念,这在当时诸多的言论和口号中就可
以明显看出,如陶成章在其著作《中华民族权力消长史》中这样解释:“所谓中国民族,一名汉族,自称中华人,又称中国人”;章太炎在其《中华民族解》中也指出,华、夏、汉为同一种意思,中华即为汉族,“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不是满洲人的中国”。从以上言论来看,建立一个由汉族自己构成的单一民族的“中华民国”的思想,普遍代表了辛亥革命前后主要思想家和革命派的思想。但是。这显然与我国的历史现实和民族状况不符。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虽然经历过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宋辽金西夏等民族分裂战乱时期,但也有过隋唐、元、明、清的大统一,而且,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统一的时间占了三分之二,分裂的时间只占了三分之一,统一始终是各民族关系的主流。所以,在我国建立西方所提倡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政权模式,显然不符合实际。也正是因为这样,孙中山由最初的“驱除鞑虏”思想转变为了后来的“五族共和”。然而,即便是这样,汉、满、回、蒙、回五族也不能代表国内的所有民族,孙中山在其晚年也反对“五族共和”的主张,如1920年11月4日他在上海中国本部会议上所作的《修改章程之说明》就指出:“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这里,孙中山显然已经看到了我国历史的民族关系和现实的民族分布状况。但他又强调:“必要满、蒙、回、藏都同化于我们汉族,成一个大民族主义国家!”这样看来,孙中山想建立的中华民国,始终挣脱不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框架,只不过在纲领上作了字面上的改变,由“驱除”到“共和”,再到“同化”。实际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模式,更多的是考虑到民族的血缘与地域的要素,这也是为什么近代我国在民族概念的阐释上更多地重视血缘和地域等要素,从而效仿西方国家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原因之一。近代我国社会面临着内患外忧的双重夹击,我国在借鉴西方资产阶级民族运动成功经验的同时,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具有中国实践的探索,这在以孙中山等人为首的筹建中华民国的过程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应该说,孙中山等人也意识到了中国的多民族状况,从“共和”、“同化”等词句来看,他们实际也在努力寻找与西方建立民族国家不同的方法,即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道路,但这始终还是单一民族国家的模式,虽然方法不同,核心还是西方的民族理论内容,并不适应我国的民族实际,因此不能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就民族概念来说,西方资产阶级学者都强调了血统的因素,这对我国近代学者、思想家、政治家的影响尤为深刻,如梁启超、蔡元培、、柳亚子、孙中山等人在给民族下定义时都视血统为构成民族的第一要素,从孙中山等人所倡导的“驱除鞑虏”、“五族共和”、“同化于汉族”等口号来看,虽然体现的是政策的演化过程,但其中以血统来划分民族的意图却也一览无余。不可否认,近代中国的民族概念更多地融进了国家实体观的意识,所谓的“谓他人而自觉为我”,以血统的差异来区分中华民族和西方民族,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套用此观点来阐释我国各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大杂居、小聚居、错居杂处的分布格局时,却又难以自圆其说。所以,提倡西方理论的中国化,“化”字是关键,既要符合中国实际,又要能解决实际问题,还要形成自己的理论。
3、提倡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构建中国民族理论话语体系,关键的是要有创新的精神,形成适合本国实际的理论。真正能够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落到实处的是中国共产党,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进行民族识别工作则是中国共产党正确阐释我国民族现象和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独创之处。在一定的意义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针对于的“五族共和”纲领而言的,前者注意到了我国各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元文化而又融合发展的现象,提倡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而后者则忽视了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彼此独立性,欲以整合的方式来泯灭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性,具有较强的种族主义色彩。两者的相同之处都借鉴和引进了国外相对成熟的理论经验,不同的是在借鉴西方的民族理论时,没有将西方的理论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生搬硬套西方国家民主建国的思想,在“五族共和”的纲领受挫时重申“三民主义”思想,但“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提倡满、蒙、回、藏四族“同化于汉族”,这难免又陷入了种族主义的漩涡中,不符合我国自秦汉时期起就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多元文化格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引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来解决我国实际的民族问题时,也经历了长期的探索过程。建党初期,我党效仿苏联实行联邦制的同时,注意到我国历史的民族关系和现实的民族发展状况,也试探性地提出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策略,经过了长期的探索和实践,最终于新中国成立前抛弃了苏联的联邦制,确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历史上,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现实,使历代统治者意识到了“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并据此提出“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原则,羁縻制和土司制就是这种原则的集中体现和具体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虽然与羁縻制、土司制等有本质上的区别,即人民自治与统治者自治的区分,但是,其中一脉相承的,就是继承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传统,适合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大分数、小聚居的民族分布状况,既能适当满足各民族的政治权力要求,又能促进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繁荣。这既秉承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原则,又是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创新。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建立健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更好地实施民族政策,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如果说,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对我国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从整体上去认识和把握,那么,进行民族识别则是对我国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的实际类分和具体化分析。民族识别在理论上的最大突破之处就是对斯大林民族定义进行了质疑和修正,“名从主人”原则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我国民族概念“中国”元素的坚持,这也符合列宁所提出的进行民族问题分析时“要考虑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的思想。对于民族的形成,早在1882年,马克思就有“部落联盟是与民族最近似的东西”的论断,∞恩格斯也提出了“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的观点。所以,对于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并不能完全概括我国各民族的全部特征。这样,我国的民族识别与其说是对斯大林民族概念的一种“软”抵制,倒不如说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形成理论的具有现实意义的实践性验证。正是我国在民族识别过程中既尊重历史,又不拘泥于理论的实践性探索,才真实地还原了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面貌和社会现实。不仅如此,20世纪80年代末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提出和21世纪初期党中央国务院对我国和谐民族概念的阐释,也都是我国长期以来坚持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创新的结果。
Articles are uploaded by users and are for non-commercial browsing only. Posted by: Lomu, please indicate the source: https://www.daogebangong.com/en/articles/detail/ppssn20064cs.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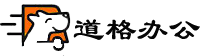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196条)
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