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衡哲(1890—1976年)是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回国后任教北大,是中国第一位女教授。她在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西洋史》是民国年间最早的世界史教材之一。截至1949年,这部教材已经连续再版9次。1943年,陈衡哲应之邀到访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红岩村,对她说:“陈先生,我是您的学生,听过您的课,看过您写的书。”[1](p.111)陈衡哲及其著作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近年来,陈衡哲的《西洋史》继续受到关注,上世纪末辽宁教育出版社再版了《西洋史》,进入21世纪后东方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岳麓书社也纷纷再版此书。这样的出版密度在同类史学著作中并不多见,可见此书作为中国的世界史教材具有一定代表性。但国内学界对陈衡哲及其著作的研究却非常有限。就笔者所知,仅有何成刚、张安利的“一部‘带有创作的野心的’历史教科书———陈衡哲著述〈西洋史〉教科书特色述评”和黄蕾“陈衡哲史学成就论略”两篇论文。因此,本文试图以《西洋史》为着眼点,对陈衡哲的世界历史观做一初步考察,并希望以此为窗口,探寻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历史观。
一陈衡哲的世界历史观有一个重要的现实基础,那就是反对战争,主张建设一个和平的世界。这一思想基础与她生活的时代及其人生经历有很大关系。陈衡哲赴美留学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她虽身处当时最安全、最繁荣的美国,远离战火,但她还是关注着战争。1916年8月,在东美学生会第12次年会上,陈衡哲参加了中文演讲比赛,并获得第二名,当时她演讲的题目就是“平和与争战”[2](p.65)。
可见,那时的陈衡哲已经开始对战争进行反思了。1920年回到中国后,国内的动荡也使她深受其苦。正如《西洋史》上册的第六版序言中所说:“此书的生命和下册一样,都是在枪声炮影中得来的———前者作于内战的四川,后者作于齐卢战争的南京。”[3](《原六版序》,p.3)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撰写《西洋史》上册的时候,她曾随丈夫到过四川,当时四川的贫穷、落后和闭塞使她非常震惊。1922年,她发表了《四川为什么糟到这个地步?》,文中历数四川的弊端,并将这种乱局归因于军阀混战:“第一个重要原因,是政界———等于军界,因为四川此时除了军事,没有别的政事。”[4]于是,陈衡哲夫妇联合报、学、商界的朋友,在重庆发起成立一个“裁兵促进会”[5]。正如她在给胡适的信中所说:“我现在做的事是(一)编西洋史大纲。(二)为川中的青年制造一点反军阀的心理(演说、文章或在言论社交之间)。”[6](p.70)
所以说,陈衡哲的世界历史观明显带有着时代的烙印。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她渴望和平,希望能用和平的方式制止武力冲突。为此,陈衡哲在《西洋史》中阐释了三个遏制战争的方法。首先,摒弃狭隘观念和阴暗心理。在对历史进行总结后,陈衡哲认为贪欲和仇恨是导致战争的重要原因。例如,在谈到上古时期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入侵时,陈衡哲这样写道:“游牧人领着他们的牲畜,到处去寻水觅草,不免时时要侵犯那土著人的田林。他们又看见土著生活的安乐,不免又起了羡妒的念头……什么日尔曼人的入寇罗马,阿剌伯人的北犯欧洲,都不过是这两种人民的战争罢了。”[7](p.20)在谈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时,她强调了斯巴达对雅典繁荣的“又恨又妒”以及雅典人的反斯巴达心理[7](p.87)。因此,陈衡哲相信,只要能摒弃这些狭隘的观念和阴暗的心理,战争就可以避免。其次,揭露军人政客的黑幕。在陈衡哲看来,战争主要是受了个人行为的影响。她从反正两个方面对此进行说明。
反面的例子是促使普法战争爆发的富于煽动性的“爱姆斯公文”,她认为“酿成这个战争的情形,是最能表现军人政客愚弄人民的罪恶的”[8](p.261)。正面的例子是在整部《西洋史》结尾所引用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记》:“美国的内战是已经开始了,英国因与北部诸州的争执,看上去似乎也要牵入战争的漩涡了,于是路索爵士便以一个极严重的公文送呈女皇(维多利亚)。但亲王(阿尔白特)觉得,若不把这个公文的语气改变一下,战争将不可免。在十二月一号的早晨七点钟,他从床上起来,用战抖的手写了一些意见,使这个公文的语气可以变为缓和,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也可以因此得到一个和平的道路。”[8](p.325)
既然这些军人政客可以左右战争,那么让民众了解军人政客的内幕就可以阻止战争的爆发。正如她在《西洋史》中所指出的那样:“我的编辑《西洋史》有两个动机。其一,是因为近年来读史的结果,深悟到战争是一件反文化的事。但同时,我又信战争是一件可以避免的事。避免的方法虽不止一端,然揭穿武人政客的黑幕,揭穿他们愚弄人民的黑幕,却是重要方法中的一个。”[7](《序》,p.1)第三,实现和平的根本方法是培养国际主义,使国际主义战胜帝国主义。陈衡哲这样阐述国际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目的及其相互关系:“国际主义的目的,是在求人类的彼此了解,及各国文化的成为世界的共产;他的重要工具,是世界的永久和平。帝国主义的目的,则适与国际主义的相反,他是以增加人类的误解及怨仇为任务的;他的重要工具,是战争。所以这两个现代文化势力的竞争,即不啻是战争与和平的竞争。使国际主义而能战胜帝国主义,那么,和平的梦想,即可实现。”[8](p.324)由此可见,陈衡哲把国际主义看成是实现世界和平的最终解决方案。对和平世界的追求,使陈衡哲把世界历史的重心放在了文化方面。综观陈衡哲的《西洋史》,反对武力、强调文化交流成为全书的主基调。
这种世界历史观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文化是世界历史的重要内容,文化兴衰是各国历史变迁的重要表现陈衡哲在《西洋史》导言中明确提出:“我们当把文化作为历史的骨髓。”[7](《导言》,p.4)因此,文化的内容在《西洋史》中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例如在讲到希腊时,关于希腊文化成就的篇幅与讲述希腊历史的篇幅大体相当。《西洋史》中对文艺复兴的系统分析表明,陈衡哲十分看重这一文化现象,称之为“西方近代文化的总渊源”。她还撰写了小册子《欧洲文艺复兴小史》,自述其写作原因是:“因为我今春编纂那本《西洋史》中的文艺复兴章时,曾处处感到不能尽意的苦痛。我曾极力的削足适履,去求减少他的篇幅,但结果仍得到了一个在一万三千字以外的长章;而我对于文艺复兴所欲说的话,却仍是未能尽其什一。”[9](《序》,p.1)就篇幅而言,《文艺复兴》这一章在《西洋史》中并不突出,但是这个文化味道最浓的章节显然是作者最钟爱的部分。又如第六版对章节目次进行了规模较大的调整,第五版中的“埃及”、“两河流域及其西邻”、“希腊”和“罗马”,在第六版中变成了“埃及古文化”、“西亚古文化”、“希腊古文化”和“罗马古文化”。陈衡哲对文化的强调由此可见一斑。陈衡哲认为,文化兴衰是各国历史变迁的重要表现,在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兴衰中,文化的力量远远大于武力的力量。这从陈衡哲对武力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论述中得到了体现。首先,陈衡哲在《西洋史》中阐述了武力对文化的破坏。她从上古史中总结出一个“埃及模式”:埃及文化在金字塔时期进入了黄金时代,可谓“外无侵寇,内无争乱”,王国在建筑、商务等方面都获得了巨大发展。但后来海克萨人(现译喜克索斯人)“把埃及占据了。后来又来了些希伯来人,他们帮着海克萨人来收埃及的税,管埃及人的民事。这两族人民一来,竟把好好的一个埃及国逼为一个尚武之国了……埃及人居然靠了武力,把异族赶了出去。但不幸就此动了征伐外族的念头。”[7](p.34)
而武力扩张最终导致了埃及的衰落。简单地说,“埃及模式”遵循了这样一个轨迹:文化繁荣———外族入侵———被入侵民族变得尚武———走向侵略扩张———文化衰落。这个模式除了适用于埃及,还可适用于西亚的亚述人和近代的日本人。此外,在论及古罗马文化时,陈衡哲用几乎全部的罗马历史论证了一个观点:破坏共和和葬送帝国的“乃是罗马自己的武功,和那个武功所产生的效果”[7](p.132)。其次,陈衡哲承认武力有时也会起到一些积极作用,但这只是“偶然的”,实不足取。她说:“武力是帝国的重要分子。所以帝国的成立是一件反文化的事,但他的结果,却常常能得到些意外的进步。我们须要明白,原动力和意外的结果———又名“副产品”———的关系完全是偶然的。历史上有许多进步,许多文化事业是万恶原动力的意外结果。帝国主义便是一个例。但意外的结果总是意外的,总是靠不住的。”[7](p.35)第三,武力虽然可以破坏文化,但不能彻底毁掉文化,文化要素还可以保留下来,因此文化的力量要远大于武力。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她指出:“武力的胜利在一时,文化的胜利在永久。”[8](p.44)
这是她在《西洋史》中阐发的中心论点之一。
(二)科学发展与文化交流是历史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也是推动世界走向文化“一国化”的重要因素在《西洋史》中,陈衡哲从历史的视角提出了一个和平世界的理想:“一个国家个性的要素,乃是一个共同的过去,和共同的将来。具体而言,即是一个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信仰……他日全世界的人类,如能创造一个共同的历史,如能发生一个共同的信仰,那么,全球便不啻成为一个国家……而近世因列国个性发达过分,而生产的混乱局面,也可以像封建制度一样,被一个更为伟大的势力去扫除了。这岂不是值得我们梦想的一个希望吗?”[8](pp.49~50)
在此,陈衡哲以国别史来推论世界史,提出世界各国在文化上的“一国化”,希望通过这一途径而达到消除混乱局面,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世界文化走向“一国化”是否可能?陈衡哲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有“科学”这个重要因素。她论述科学的作用说:“近代的科学,直接的既已成为一切学问的基础,一切进步及人类谋求幸福的工具;间接的又靠了工业革命的势力,成为工业、商务以及政治、社会、一切事业的原动力。他实是近代文化的中心点。不但如此,他又能不问宗教,不问民族,不问语言,不问天然或地理的限制,但知以真理赐与全世界人类,所以科学又是一个可贵的国际势力。”[8](p.293)
由此可见,在陈衡哲看来,“科学”具有跨宗教、跨民族、跨语言和跨国家的特征,是全人类谋求幸福的工具,既能够为各国普遍接受,也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科学”的这些特性,使它成为推动世界各国文化“一国化”的重要力量。除了“科学”之外,陈衡哲认为,文化交流也是实现世界“一国化”以及世界和平的重要手段。在《西洋史》中,文化的交流乃是贯穿全书的重要内容。在该书第一编的结论部分,陈衡哲指出,文化交流推动了上古历史的发展。这种观点渗透到书中的许多章节中。文化交流如何促进文化融合与世界和平?陈衡哲在《西洋史》中对此并未进行具体阐述,尤其是对于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交流涉及很少。但是,她在另一篇文章中给出了答案:“这种中国旧有美德与现代西方新文明的结合不是随意的混和,也不仅是相互的迁就,而是一种原本彼此呼应的因素之间的和谐融汇。”[10](《译者前言》,p.25)因此在陈衡哲看来,文化交流不应是简单的“物理变化”,而应是可以使文化达到和谐融汇的“化学变化”,通过这种“化学变化”而创造出一种更先进的共同文化,这种共同文化即可成为“一国化”的基础。
(三)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各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道路可以有多种选择陈衡哲虽然提出了全球文化“一国化”的理想,但是在总结了欧洲及亚洲国家的历史变迁之后,她对亚洲国家的政治及社会发展道路进行了思考。在《西洋史》的最后一章,她指出了亚洲国家发展的三条道路:“亚洲的人民却只有三条道路可走。其一,是效法列强的武备以自救;其二,是因不肯效法而沦为列强的奴属;其三,是凭着自己的天才,另去创造一个新道路。第一类的代表,是日本;第二条的代表,是印度;而彷徨于这两条歧路之间,而又未能另自创出一条新道路者,则有我们的中国。”[8](p.313)
这一概述,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亚洲现状的思考。各国的国情不同,在西方霸权面前,它们可以选择不同的应对方式和发展道路。对于中国来说,以日本和印度为代表的道路行不通,因为这两条是“歧路”,中国应该“凭着自己的天才”,“去创造一个新道路”。但遗憾的是,在陈衡哲所生活的时代,她看到的是中国“未能另自创出一条新道路”,而是正处于“彷徨”之中。她希望中国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自己创造自己的命运。她认为自己创造自己的命运非常重要,这点在她的一篇寓言散文《运河与扬子江》中有所体现。这篇文章模拟大运河(代表被人创造)与扬子江(代表自我创造)的对话,她借扬子江之口说出:“你不懂得生命的意义。你的命,成也由人,毁也由人;我的命却是无人能毁的。”[11]由此可见,她认为,日本和印度的道路都是列强强加的,是对外来势力的屈从,这样的命运“毁也由人”。中国只有走出自己的道路,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成为自己的主人。因此,在《西洋史》中,陈衡哲叙述的虽然是以西洋为主的世界史,但是她所思考的却是中国的命运和中国的发展道路。
二陈衡哲的世界历史观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尚处于起步阶段,她的《西洋史》及其世界历史观对于世界史的教学、研究和学科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陈衡哲引入了美国先进的历史教学方法。在就读瓦莎大学期间,指导陈衡哲的是两位很有能力的教授:历史系主任露西•沙蒙(LucyM•Salmon)和欧洲史教授埃勒维兹•埃勒雷(EloiseEllery)[2](p.36)。她曾选修露西•沙蒙的“新闻纸的历史价值”课程,考试时老师把学生带到图书馆,发给每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从下面的报纸中,编出那一个时代和地方的小史来。”这种考试形式非常新颖,突出了寻找史料和运用史料的基本功。这使陈衡哲受益匪浅,她体味到教学过程中启发引导和师生互动的重要性,这对她以后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产生了深刻影响[2](p.41)。
回国执教北京大学后,她将这种方法引入其世界史教学,鼓励学生自己寻找史料。但是在当时,即便是在北大,可用的材料也并不是很多。正如陈衡哲所言:“(编著《西洋史》的)第二个动机,是我三年前在北京大学教授《西洋史》时所得到的。我是最反对注入式教育的一个人。在史学界中,这个方法尤为无益有害。所以我曾特别注意学生的自己搜求材料,作为辅助或是证明我的演讲之用。但这个努力的结果,不过使我感到中文参考书籍的缺乏。于是我便决意辞去教职,专门编书。”[7](《序》,pp.1~2)
所以说,《西洋史》本身乃是实践国外历史教学法的产物。这种方法摒弃了“注入式教育”,为沉闷的世界史教学注入新鲜空气,也是陈衡哲对文化交流和借鉴的亲身实践。其次,陈衡哲为当时的世界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在20世纪20年代,世界历史在中国是一门新兴学科。当时,世界史应该研究什么,应以何种观念进行研究,都在探索之中。陈衡哲在《西洋史》中回答了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研究范围。陈衡哲所写的是欧洲史,但这个欧洲不是“地理的欧洲”,而是“文化的欧洲”[7](p.27),所以除了欧洲之外,该书还涉及了西亚北非地区。按照作者的计划,该书还应包括“欧化”的美洲,但由于篇幅所限,这本著作中并未包含美洲部分。但是《西洋史》的讨论范围还不仅限于此,书中的许多论述都涉及亚洲,上文提到的亚洲国家的三条发展道路就是个例证。在讲到新帝国主义的时候,她还特别写了中国。换句话说,陈衡哲的世界历史观是包括中国的,而且中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她的世界历史观体现了一种整体史的思路。这一思路是作者重点强调的,例如,在谈到研究历史的目的时,陈衡哲写道:“我们所要研究的不是某某皇帝的家谱,也不是武人政客的行述,乃是我们人类何以能从一个吃生肉的两足动物,变为一个代表现代文明的人……现在我们研究的范围,虽然只以西洋各国为限,但无论哪一部分人类的历史,都具有普通和特别的两个性质……普通的性质,是人类所共有的。所以我们研究了人类一部分的历史,不但可以了解那一部分的人类,并且可以了解自己的一部分。”[7](《导言》,pp.1~2)由此可见,陈衡哲的整体史观念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她认为世界历史应该研究人类全体,而不是某一特定地区的人;二是虽然她所写的是欧洲史,但她希望从中得到一种跨越民族和国家界限的普遍规律,这个规律适用于整个世界,中国当然也包括其中。但遗憾的是,在世界史日后的发展过程中,中国逐渐被排除在外,于是世界史变成了没有中国的世界史,这不得不说是世界史研究中的一个缺憾。第二个问题是研究观念。陈衡哲强调世界历史中的文化和文化交流,她所理解的文化是一种广义文化,它“不单是政治,也不单是经济或宗教,乃是政治、经济、宗教以及凡百人类活动的总和”[7](《导言》,p.4)。
在世界史研究中以文化和文化交流作为主线,这一观念不仅在当时为世界史学者提供了研究思路,甚至对于当今的世界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为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宏观世界史或曰全球史就非常关注整体史和跨文化交流,其理论和方法与陈衡哲的世界历史观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再次,陈衡哲的《西洋史》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欧洲中心论”,从受压迫国家的角度思考世界历史,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当时的“西洋史”类著作往往以欧洲的视角看待世界历史发展,但陈衡哲的《西洋史》却并非如此,该书对欧洲发展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提出了批评,对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殖民侵略尤为不满。在讲到新帝国主义时,陈衡哲提到了中国,她写到:“新帝国主义最大的目标物,即是大宗的原料,投资的机会,及消耗盈余出品的商场,于是我们中国便成为他们最好的目的物了。原来我国的原料是最为丰富的,投资的机会是最为广大的,人民不但繁庶,而且又是最能消耗‘洋货’的,这岂不是列强资本家的乌托邦吗?”[8](p.305)
显然,她是站在中国的角度来看帝国主义,而不是站在欧洲的立场上叙述殖民扩张。又如,谈到未来发展时,她认为各国应该“以己国对于文化的贡献,视为国家荣誉的标准者,于是他们便能以藏兵毁甲为发达国家个性的第一步骤了。这犹之高尚孤洁之士的不以富贵利禄而以一己的人格来作为生命成败的标准一样”[8](p.324)。
不以富贵利禄为荣的“高尚孤洁之士”是比较典型的中国士大夫形象,可见陈衡哲希望中国的道德准则能够成为未来世界的标杆之一,这个呼吁再次体现了她对中国文化本位的坚持。此外,陈衡哲指出的亚洲发展的三条道路,其中日本是西化的代表,但这正是她所否定的。因此,陈衡哲显然是不赞同“全盘西化”的,她的世界史观并没有陷入“欧洲中心论”的陷阱。陈衡哲的世界历史观有许多可取之处,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她的“精英意识”上。陈衡哲的出身和成长经15历是造成这种精英意识的主要原因。她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之后又受到良好的教育,因此她自己就是精英阶层中的一员。正如冯进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陈衡哲显然认为自己能称职地担任一个与外国读者交流,告诉外来世界一个真正中国的文化代言人。她把自己的经历说成具有代表性普遍性的做法正是她试图向外国读者确立自己资格的关键步骤。然而陈的这一做法其实造成了一个她不能解决的悖论,即,她根本不是大时代里一个普通的中国人。”[10](《译者前言》,p.15)
陈衡哲认为知识精英可以担当中西沟通的历史重任。但实际上,这些高高在上的精英们既不能代表整个中国,也不了解中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这不得不说是陈衡哲世界历史观中的一个不足之处。陈衡哲的精英意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陈衡哲认为能担负起文化交流使命的精英人物是历史的主人公。在1935年一篇文章中,陈衡哲将女性分为天才女子和普通女人两类,她认为前者要走出家庭贡献社会,而普通女人要相夫教子[12]。如果将这一逻辑推而广之,那么就可以笼统地将社会分为“精英”与“非精英”两个阶层。陈衡哲是如何理解“精英”的呢?在《自传》中她写到:“我们家在经济上并非大富之家。但过去在中国金钱并不受重视,特别是读书人常常以他们的清贫自傲。”[10](pp.22~23)
她在后文又写到:“我家属于士大夫阶级……这个阶级有自己的自负和偏见……士大夫阶级总把学问上的成就和个人品德看得比什么都重,并且对也好错也罢都以此为标准来判断人。”[10](p.50)由此可见,作者心中的“精英”并非当时西方所看重“政治精英”、“经济精英”,而是“文化精英”。陈衡哲自己显然就属于“文化精英”中的一员。因此,在《自传》结尾,她特别将中国派留学生赴美深造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提并论,并突出了女留学生的作用:“耐人寻味的是,当整个世界将要被这场巨大的军事冲突改变时,中国的整个国民生活也将因为政府首次派遣女生留美而发生巨变。这是因为,和过去政府派到西方国家的许多年轻男子和特使不同,这些年轻的女孩不是被派到西方国家去建立政治或军事方面的关系的。她们被委派去学习西方国家的文化。这种对文化的强调培养了日后许多美丽的友情,最终在人们的心中———而不是在播种战争的政治领域,为一种无形但强大的联盟的建立撒下了种子。”[10](pp.174~175)
陈衡哲相信文化交流是国际和平的重要途径,因此她留学的意义也就溢于言表了。简单地说,陈衡哲的精英观念与强调文化交流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在她看来,只有精英才能担负起文化交流的重任。另一方面,虽然同情一般民众,但陈衡哲并不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并不认为他们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因此,她根本不可能将人民群众———尤其是下层民众———视为历史的缔造者或救国于危难的人。这一点在《法国革命》一章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七月十四日的那一天,那一群巴黎的暴民,便携棍带斧的去攻那个古堡。他们残杀了看狱的兵士们……自此,法国革命中的暴民政治就开始了。”[8](p.201)
将法国大革命视为“暴民政治”不是《西洋史》的首创,但如此描述轰轰烈烈的攻占巴士底狱这一重大事件似不多见。她将巴黎人民称为“暴民”、“流氓”和“游民”,还在文中突出了民众的贪婪,“人民又希望宪法一成,租税可以从此不出,面包可以不劳而获”[8](p.202)。
在谈到法国民众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时,书中写道:“下级的贫苦农民和工人,也始终是革命的打鼓敲锣者;中等社会……是那个运动的重要主人翁,平民不过做做他们的马前卒,为他们摇旗呐喊,助助威风罢了。”[8](p.227)
综上所述,陈衡哲的世界历史观虽然存在不足之处,但对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启迪意义。从研究视角来说,陈衡哲强调文化与文化交流的意义,这是世界史研究的一条重要思路。从教学实践层面来说,她所引进的教学法至今都有借鉴价值。从治史理念来说,她的西洋史中也包括中国,陈衡哲一方面从中国的角度认识世界,另一方面又以世界历史来启发中国的发展之路,这些都为当今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提供了启示。
文章为用户上传,仅供非商业浏览。发布者:Lomu,转转请注明出处: https://www.daogebangong.com/articles/detail/pzcf1k0532ax.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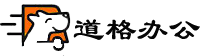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196条)
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