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间苦难本身具有双重意味,莫言以大悲大欢的笔墨,呈现残酷美学,把我奶奶、母亲、姑姑,上升为象征性的文化符号,用来直观历史、现实和人性伦理。《红高粱》中戴凤莲说,“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这个质询恐怕不单纯是一个女子对生活的疑问。余华在《谁是我们共同的母亲》中评价说:“莫言在《欢乐》里歌唱母亲全部的衰落时,他其实是在歌唱母亲的全部荣耀,他没有直接去歌唱母亲昔日的荣耀,是因为他不愿意在自己的歌唱里出现对母亲的炫耀,他歌唱的母亲是一个真实的母亲,一个时间和磨难已经驯服不了的母亲,一个已经山河破碎了的母亲。”[4]余华认为读者在小说中寻找和确认的不是个人的母亲,而是抽象出来的意象化的共同母亲,所以莫言对母亲形象的某种僭越激怒了抱定母性崇高信仰的人们。莫言写大地,写母亲,不仅仅在和人性伦理较量,还有对文化母体的解剖,甚至凌迟。那么,他在打量着一切的时候,内心究竟在想些什么呢?世界性意味着什么莫言小说不仅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而且张扬那种凌厉的现代小说精神,现代意识和民族文化结合点是精神寻根。那些封闭、凝滞的文化阴影和心理投射,与敞开、流动的现性遥遥相望,批判反省,常常以沉湎戏拟的方式藏在喧嚣与躁动的文字背后。莫言把高密东北乡从尘封的民间打捞出来,然后以世界性的眼光,打造成人类生死爱恨的社会舞台和历史时空。高密东北乡的精神领地不断丰富,莫言给了这个虚拟的地理位置以文化视野的无限延展性。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后,莫言曾说:“我有野心把高密东北乡当作中国的缩影,我还希望通过我对故乡的描述,让人们联想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5]“福克纳的那个约克纳帕塔法县始终是一个县,而我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就把我的高密东北乡变成了一个非常现代的城市。”这种变化“不仅仅是地理和植被的丰富与增添,更重要的是思维空间的扩展,这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6]。自五四以来,我们一直在追求文学的世界性表达。中西文化交流的方式日渐多样,但并没有在同一层面真正做到平等对话,西方文化始终以强势姿态高高在上,当然,这与我们近代以来被迫形成的弱国心态直接相关。新文学传统在西方文学巨大的阴影下慢慢生成,1980年代西方影响的焦虑感伴随民族文化认同危机感,再次席卷而过。当代中国作家写作,面临数次话语转型,从政治话语转向民间话语,从理想主义转向世俗主义,从民族立场转向普世价值,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思,始终建立在西方文化坐标系上,作为他者文化,构成现代性的尺度。以前,国人常说诺奖有政治偏见,有文化歧视,有语言障碍,这些因素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毕竟不是最主要的。回顾沈从文和老舍的东方审美,同样具有民族文化认同感及人类共同性,探索人类存续的根本问题,有生命感知的从容,语言也优美。莫言有所不同。莫言小说多为双声部,一面是传统文化的喧哗,一面是现代意识的躁动。我们读他的小说,时刻感受到他奇异的眼光,在中国式村庄和世界视野里跃动,现实主义的严肃往往被幻化的艺术技巧所拆解和遮蔽,这种视角位移增加了时空错杂的内驱力和离心力。莫言小说对客观世界的呈现不是平铺直叙的,主观感觉世界更是幽暗曲折繁复,他把个人放在特殊情境下,挤压、撕裂,放大了人性的复杂。有研究者指出,莫言小说对传统文化和中国历史负面形象的聚焦:残酷的刑罚,暴力,,,饥饿对人的折磨和扭曲,无节制的语言狂欢,只是为了迎合西方的审美标准。这么说显然不公平。从《透明的红萝卜》开始,莫言就被看成先锋作家。对于1980年代中后期盛极一时的先锋文学,二十年来评价莫衷一是,唯文学观念的嬗变和叙事技巧的探索来自于西方已是共识。《红高粱》标志着莫言小说形成审美自觉,尤其是叙事情感方面,那种激昂壮烈、冲决一切的爆裂风格,于古老的乡土中国是一次巨大的精神震荡。莫言对威廉•福克纳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写作很熟悉,他承认自己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魔幻现实主义对我的小说产生的影响非常巨大,我们这一代作家谁能说他没有受到过马尔克斯的影响?我的小说在86、87、88年这几年里面,甚至可以明显看出对马尔克斯小说的模仿。”[7]《十三步》情节荒诞,人物变形,以此代彼,生活充满魔幻,叙事上也带有实验性,是很典型的先锋小说。《酒国》在艺术技巧上达到了莫言小说的新高度,既有民间和传统文化韵味,也有叙事上的大胆创新,“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实验性文体。其思想之大胆,情节之奇幻,人物之鬼魅,结构之新颖,都超出了法国乃至世界各国读者的阅读经验”(法国“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授奖辞)。莫言说:“在结构上我比较满意的还是《酒国》。一方面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另外,在语言上进行了多种多样的戏拟,游戏性地模仿当时各种各样的文体。小说的整个组成包括虚与实两大部分,一方面我作为作家写一篇反腐侦探小说,同时又有一个文学爱好者给我通信,把他写的小说寄给我,后来我的小说与文学爱好者的小说融为一体,人物互相参照、印证。事件也是这样,最后结尾,作家真的到了文学爱好者的故乡那里去,发现这个在小说中桀骜不驯的人其实是个唯唯诺诺的小职员,最后小说中的主人公喝得醉醺醺的掉到茅坑里淹死,作家在酒国里也醉得昏天黑地。……我认为在小说结构上它是比较巧妙的一部,而且我也知道它不为大多读者接受是非常正常的。”[2]另一方面,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是相对而言的,二者有着内在的互文性。莫言写的是中国故事,是典型的本土写作,乡土叙事的脉络梳理出最中国的故事和浓郁的中国风格;在世界文化版图上,莫言贡献了一种中国化的叙述图景,即西方审美的中国形象。形式借鉴现代西方,故事扎根传统中国,又兼有社会现实批判,这是莫言小说的基本要素。
历史理性与世俗狂欢
一个人对文字的追逐,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像一条生命的河流,我们看得到它的波光粼粼,却不一定了解它的源头;一个人对文字的信任,开始于什么时候?是对世界以质询的眼光凝视,还是在浓黑的历史和文化暗区里,发下立言的盟誓?莫言的文学世界错综复杂,诡黠怪诞,呈现出一种极为复杂的结构,也不乏重叠交错、自相悖谬的立场。他的小说首先将人的活动还原到一种物质性和生理性的层面,从人的基本生存活动出发,充分展示了日常生活直观层面的光怪陆离,以及深层的历史文化的复杂性。所以,评价莫言小说创作,研究者大体会将其放在寻根文学、先锋文学、乡土文学、新历史主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暴力美学、齐鲁文化等范畴中。这些标签,于莫言而言,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只是看取莫言写作的不同视角而已。考察一位作家对待历史和现实的态度,往往是我们走进其文本世界最近的道路。莫言笔下,充满诗意的民间大地,承受暴力和血腥的与农民命运生死攸关的土地;野地里无限张扬的人的本能和性情,在宏大历史和现实困境中不断萎缩退化的民族血性,两种不同方向的力量分裂着人的感知世界。(一)在历史的平衡木上摇摆历史反思,文化批判,现实关怀,忧患意识,审美自足,莫言有属于自己的寻找人生和重建世界的方式,这个过程,就是高密东北乡这个想象世界的建构。高密东北乡,虚构的世界里,生存是真实的,残酷的,逃不出历史的定律和生死轮回。莫言的历史观很复杂,民间史观,民族史观,唯心史观,都有,谈到历史态度,莫言说:“我认为小说家笔下的历史是来自民间的传奇化了的历史,这是象征的历史而不是真实的历史,这是打上我的个性烙印的历史而不是教科书中的历史。但我认为这样的历史才更加逼近历史的真实。因为我站在跨越阶级的高度用同情和悲悯的眼光来关注历史进程中人和人的命运。”[8]这种个人化、个性化和生命化的历史观,有着文化多元和思想边缘的时代特征。他的解构和建构是进入历史的双向通道,民间原生态历史的复现,摆脱了正史的静态框架和庄正风格,戏谑嘲讽放纵狂欢,给历史、生活和人,都披上了神魔奇幻的外衣。苦难与挣扎,放纵与喧哗,与躁动,阴郁与死寂,既是一部历史的传奇,也是一部变形的历史,更是一部以传奇和变形的方式无限逼近真实的民族心灵史诗。《生死疲劳》是莫言最好的长篇小说之一,充满偶然性和戏剧性,是对历史规定性的反叛,也是对历史另一种本质的寻找。艺术形式不是最重要的,向传统小说致敬,也不是他一个人的独创,真正的价值在于他内在的历史理性,超越轮回,黑白两色的历史躯体上布满被遗忘的伤痕。《红高粱家族》和《丰乳肥臀》是以民间生存表现历史,《檀香刑》是以民间文化去解读历史。《红高粱家族》与传统历史战争题材小说不同。我们现在谈论新历史主义小说,多半从莫言的《红高粱》和乔良的《灵旗》说起,这两部中篇同一年发表,前者在春天,后者在秋天,两部作品同时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自此,当代中国小说中的历史叙事摆脱阶级论,走向人性论。《红高粱》中的历史带有陌生感、奇异感和离散性。传统历史小说和革命历史小说中的历史是确定的、线性的、理性的,莫言笔下的历史表现为模糊的、散乱的、感性的。高密东北乡的爱恨情仇是小历史,但正是这饱满的小历史覆盖了僵化的大历史,把历史叙事带入了一个隐秘而又敞开的世界,相对于线性历史的自闭性,这一新的历史叙事给出了广阔的思想和精神维度,僭越自我幽闭和意识形态,勾勒历史之镜的背面成像。《丰乳肥臀》走得更远,生存依然是第一位的,历史和现实则是互文的,这一视角让我们看到了莫言内心的忧伤和冷峻。《丰乳肥臀》作为民族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寓言,展示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内部蕴含的文化困境、文化焦虑、文化血缘的自我清理,正如邓晓芒所说:“莫言凭他对文学的敏感和某种自我超越的灵魂,发现并抓住了我通过文化和哲学的反思所揭示的同一个问题,即我们时代各种症状的病根。”[9]莫言对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都有所批判,虽然也都不彻底,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局限,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整体局限。总体上《丰乳肥臀》的思考比较深远,《酒国》的魔幻就未免有些技巧大过内容。莫言以当代人的视角和心理,对民族历史悲剧的根源加以透视和投射,十七年以来形成的叙述历史重大题材的庄严郑重都消失了,面对去除层层包装和伪饰的民间史,他以荒诞甚至游戏的笔触、更原始的情绪和更漫漶的文字,穿越历史人生以及人性的遮蔽,发掘活着的真相。从一片壮烈的红高粱地走来,走出了根的缠绕,在历史与现实的大跨度中,人的生存焦虑、民族的生存焦虑缠绕在一起,构成来自民族内部的精神痛楚和两难困境。《檀香刑》中的历史是血腥的,《蛙》中的历史是残忍的,非正常死亡连缀起历史的影像,在放映的画面里,积满了冤魂和哭诉。谁是记忆的主体,谁来对这些记忆做出评价?(二)打开人性的魔盒人性,在中国作家笔下,往往不仅意味着普遍人性,其中还含着国民性概念,国民性,则直指非理性的文化病态。莫言喜欢草莽英雄,如《红高粱》中的余占鳌,《檀香刑》中的孙丙之类,包括上官鲁氏、戴凤莲和孙眉娘这样敢作敢当、敢爱敢恨的女子,极力渲染这些人身上的生命激情。本性张扬和人性批判,是问题的一体两面。暴力、残酷和血腥里,生存本身弥漫着人性的冷漠和壮烈。莫言对人性的挖掘可谓深刻犀利,刀刀见血,毫不留情,因而有不少读者认为其过于耽溺,自我陶醉,笔墨不加节制。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见出人性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张爱玲是个很好的例子,不张扬,不凌厉,不峻急,虽曰传奇,多半都是平常日子饮食男女。莫言获诺奖后,李银河接受“搜狐文化”独家专访时说:“莫言的小说影响还是很大的,他开创了一种很民俗的写法。我记得很早看过他的一个作品,他对色彩的感觉特别好,他的小说很像有些夸张的民间那种民俗画,色彩上喜欢红绿大对比,绚丽多彩,非常独具一格。另外,他的小说揭示了我们民族性里所携带着的那种残酷性。”她指出莫言小说带有民族性里的残酷性,抓得还是比较准的。莫言在谈到自己的写作时说,写人是唯一的目的,是用历史的环境来表现人的灵魂,人的感情,人的命运变化,小说只有描写了人性,描写了情感,才更丰富,影响更长远。莫言小说中的英雄和土匪,放荡和刚烈,重情和贪婪往往集于一身,对于人性异化和人文精神丧失,莫言不无忧患,只不过,在魔幻的现实里,这一切都带上了表演的性质,其批判性有所减弱。莫言反复向读者推荐《生死疲劳》,首先,这本书是对中国历史和现实重大问题———土地和农民问题的一种思考;其次这本书采用了一种东方式的超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小说中人跟动物之间可以自由地转化,通过动物的眼睛来观看中国最近50年来社会、历史的变化;运用了一种最自由、最没有局限的语言来表达;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对文学探索、文学创作的一种比较完美、统一的结合。写作者穿行在人性的丛林里,会看到奇异风景,也会遭遇毒蛇猛兽,勇敢者不断深入,屏住呼吸,把时间不能抹去的痕迹,那些历历伤痕,雕刻下来,就会让我们透过生活表面看到更深远的世界。莫言还提及,在自己80年代的所有创作中,最偏爱的是小说《金发婴儿》,认为“它更像一篇小说,深入到人的隐秘世界里。”[10]女主人公背叛丈夫表面上是因为寂寞,深层意识是自我价值的要求和渴望爱的人性本能,小说里暗含着人性与反人性的思索和较量。反人性的力量在压抑和撕裂女主人公的生活,人性的本能突破禁忌,达成了自由和幸福。小说给出了悲剧结局,自然人性很难突破社会身份和伦理道德的围困,存在本身就包含着进退两难的选择。《酒国》通过荒诞的情节,戏仿的手法,表达了一种现实困境:主观的向善并不能保证人性的善,无法自由选择的存在是人类所共有的痛苦根源。历史理性和生活感性就这样相互缠绕纠结渗透在莫言的文学世界之中。当然,二者之间不是没有裂隙的,莫言内心保持知识分子的清醒,常不自觉地反观自己的民间立场,这种自我怀疑,使得叙事和文本中隐含着对人本身的质诘,其实这也是当代作家共同面对的精神难题。先不说传统文化到底是不是自由人性的牢笼,即令西方的人性解放、自由平等作为普世理想,又如何落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檀香刑》《生死疲劳》《丰乳肥臀》,张扬的都是原始生命活力及的原生态张力,那种自在自为的力量,是更接近人性解放的理想,还是多半表现为一种破坏力?现代性路上,我们要面对巨大的文化惰性和历史负累;反思现代性,我们同样缺少真正可供运用的思想资源。对此,莫言不可能没有清醒的判断,他站在民间之上,遥望人类生存理想,无论以己之矛攻彼之盾,还是反之,都没有文化的合法性可供依托,因此,站在西方审美和中国故事之间,站在意识形态和民间价值之间,我们看到莫言一直在做着超越性努力。
话语体系与审美图谱
(一)声音抑或腔调话语方式,不仅是一种表达,更是一种态度,一种文化心理的传达,意味着世界观和价值判断。知识分子所选择的生存策略和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与特定的社会特征相关。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人为地形成了一种普遍意义的世界,知识分子的话语不再受地域和共同传统的束缚和制约,他们正在通过自己的个性化表达确立普遍意义上的现代性话语。福柯认为,话语即权力。话语和权力不过是同一个所指的两个能指,二者都是不断演进的。莫言小说最独特的表征是他的语言色调。有人说,莫言的小说语言如洪水泛滥泥沙俱下,有人说他富有奇思妙想,诗意盎然,起伏跌宕,灵光闪现。这些判断其实还有阅读者的个人好恶在里面。语言的内在结构可以展示语言与世界的某种关系,但是语言无法凭借自身的力量来陈述这种关系,因为陈述时需要另一语言来丈量现实与关于现实的话语之间的距离。在语言能够自由表达的极限中,语言自身包含着与外部世界显而易见的边界。莫言小说体现的是民间话语和知识分子话语的双声道。《蛙》的语言与前面的几部长篇有所不同,那种恣肆的话语狂欢收敛了许多,莫言不再沉湎于自己制造的那个王国,而是站在人类的高度,审视历史和政治,话语方式的位移,体现了他的思考不断沉潜。西方的现性与东方的生命直觉,二者的差异非常明显,何况其中还纠结着中国式的政治意图,这就给作家设定了语言涉渡的重重考验。莫言是智慧的,他以自己的话语方式弥合了二者之间的裂隙,在断裂处,生长出一个异形空间。埃斯普马克谈到:“幻觉现实主义堪称莫氏独创。他说,我不否认莫言的写作确实受到了马尔克斯的影响,但莫言的‘幻觉的现实主义’主要是从中国古老的叙事艺术当中来的,比如中国的神话、民间传说,例如蒲松龄的作品。他将中国古老的叙事艺术与现代的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需要讨论马尔克斯、君特•格拉斯例如《铁皮鼓》的影响,但我个人认为马尔克斯和格拉斯的影响不是直接的,他们真正的重要性在于让中国式的故事讲述方式变得合法了,他们让中国作家知道可以利用自己的传统艺术写作。”[11]这段话说得有点绕,也颇值得玩味。莫言有自己的语言风格,这是他最重要的写作标签之一,而这种语言风格来自于变形的民间,民间话语给了莫言很大的空间,他把福克纳、马尔克斯的风俗感,文化的神秘感,作为审美形态,植入高密东北乡的广袤土地,突破具体时空限制,由具象到抽象,由经验到超验,由神秘到神奇,由荒诞到荒芜,生命的转换,世事的变迁,想象与现实叠加,偶然与宿命缠绕,那些抓住人心的故事里,有多少对人心的解剖?莫言不停地写,不停地说,他的话语方式,似乎隐藏着无数压抑的冲动需要宣泄和释放,那个牢笼究竟是什么?是什么力量让他觉得压抑?在文化的长河中,他左顾右盼,彷徨游移,小说给了他一个自在的世界,在这个无限广阔的世界里,他把人,把历史,把文化放在手术台上,显微镜下,解剖病理,虽无药方,总有民族病态发人深省。(二)乡愁如同雾霭莫言说:“我在《枯河》里写了故乡的河流,在《欢乐》里写了故乡的学校和池塘,在《白棉花》里写了故乡的棉田和棉花加工厂,在《球状闪电》中写了故乡的草甸子和芦苇地……”[12]“高密东北乡”在某种层面上是故乡的摹写。回忆,是心灵疗伤的过程。西方哲学家马尔库塞曾言及:“回忆并不是一种对昔日的黄金时代(实际上这种时代从来未存在过),对天真烂漫的儿童时期,对原始人等等的记忆。倒不如说,回忆作为一种认识论上的功能,是一种综合。”[13]回忆作为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是人类普遍采取的平衡情绪、寄托情思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现实的规避。鲁迅的精神世界里心事浩茫、热烈而丰富,思想矛盾和阴郁之时,极易从回忆中寻觅精神的些微温暖和心灵的片刻闲静。对于莫言来说,童年生活、故乡记忆、个人生活经验、时代政治文化环境等多种因素,同样与他的生命和写作息息相关。“对于生你养你、埋葬着你祖先灵骨的那块土地,你可以爱它,也可以恨它,但你无法摆脱它。”“饥饿和孤独是我的小说中的两个被反复表现的主题,也是我的两笔财富。”[2]灵魂循着乡音,聆听世界,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以不同的身份讲述或经历那些人间的悲欢故事。以传说、记忆乃至幻想的方式返回故乡,在一个有限的空间构筑无限的时间领域,构筑象征性的文化之乡、精神之乡和心灵家园。莫言同样选取了两个维度,向后看,梦回故园,向前看,重构世界。莫言说:“我敢于把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情,改头换面拿到我的高密东北乡,好像那些事情真的在那里发生过。”“好的作家,总是千方百计地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更加广泛和普遍的意义,总是使自己的作品能被更多的人接受和理解。”[14]“作家的故乡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变化的概念。作家作品中的故乡,是不断拓展、丰富着的。就像一个巨大的湖泊,四面的小河小溪往里面涌入。发生在世界各地,天南海北的事件,各种故事,包括风土人情,自然风光,都有可能拿来移植到他最熟悉的环境里去,于我而言,就是我的高密东北乡。”[15]那片土地是刀枪不入,还是早已遍体鳞伤?莫言并非执著于乡土世界,而是以此为出发点,不断走向历史和时代深处,他向故乡寻找生存的原动力,向历史追问文化的自省力,向人性深处挖掘晦暗不明的精神野地,原乡,是他的生命依托。淡淡的血痕中,惨烈的生存背后,有他对于活着的独特理解;特定的社会语境里,原乡,与世界的快速变动相比,来得迟缓,更像一种轮回。显然,他没有给我们答案。我们读作品,听他自述,为他所吸引,或是被他的文字所伤,无论怎样,那绵延不绝的乡愁,如风入骨髓,无形,却痛在心里。没有温柔的暖意,有惨烈的激情;没有历史的崇高,有时代的壮阔;没有人的完整形态,有人心的深不见底。是故乡以永恒的姿态给了他一往无前的勇气,还是浓重的乡愁拉住了他一骑绝尘的话语狂欢?《透明的红萝卜》中的忧伤诗意,此后不再;《丰乳肥臀》里的忧患似乎更贴近乡土中国的性命攸关;《蛙》对政治的挑衅,不急不躁,延续了《檀香刑》中权力话语与民间伦理的冲突。莫言小说里不乏时代、政治和民族的三重焦虑,对原乡的执著,隐含着虚构故乡的文化理想。要不要返乡,是不是家园,有没有彼岸,莫言的文化心理机制很复杂,在这一层面,似乎很容易确证莫言与福克纳们的精神联系,深究起来,内在的冲突和断裂,仍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乡的概念有关。回头看《爆炸》一类作品,其中社会、理性、道德层面的问题意识颇为突出,不过对理想家园的建构尚未提升到生命哲学高度。弘一说,人生就是悲欣交集。读莫言小说,感受大体如此。悲叹夹杂狂欢的叙事潮起潮落,如秋阳映照大片红高粱,土地冷而荒芜,红高粱独自燃烧成一片血色的海洋。莫言在法兰克福讲到:“一个国家的文学想要取得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同样也要具备自己的鲜明的风格,跟别的文学在基本点上有共同的地方,但某些特性要十分鲜明。所以我想,中国文学既是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也是属于中国自己的,这才是对的。那如何实现这一个目标,这就需要我们在向中国古典文学、西方文学包括德国文学学习的同时,去发掘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所蕴藏着的创作资源,包括我们每一个人与别人不一样的亲身经验。”[1]莫言的小说艺术并不完美,他只是一直在尝试用自己的方式讲述他的中国,讲述他的故乡。他诚心正意,热爱生活,关注现实,求解历史,忧患未来,殊为难得。
作者:张艳梅 单位:山东理工大学
文章为用户上传,仅供非商业浏览。发布者:Lomu,转转请注明出处: https://www.daogebangong.com/articles/detail/pz19kz053kqn.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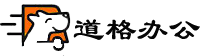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196条)
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