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汤姆·冈宁
译者:覃天
校对:易二三
来源:The Palgrave Handbookof the Philosophy of Filmand Motion Pictures(2019年)
如果人们用「诗意」来描述一部影片,这意味着什么?批评家可能会把一部电影或电影中的某个片段称为「诗意的」或「抒情的」。
人们也常用「诗意」来描述泰伦斯·马利克、亚历桑德罗·佐杜洛夫斯基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或是费德里科·费里尼作品的视觉风格。

《乡愁》
此外,像玛雅·黛伦、让·爱泼斯坦这样的非主流导演也常将自己的作品称为「诗电影」,从而和大多数的商业电影区分开来。我们是否可以梳理电影理论中对「诗意」一词的使用?在本文中,我希望能探讨这一词义的含义,并分析「诗电影」一词在批评分析中可能的有用性(以及危险性)。
在文学批评和理论中,似乎可以通过某些可识别的形式——韵律、节奏、页面布局,将诗歌与散文或其他的文学形式进行区分。要理解诗电影,我们必须回溯这一文学传统。将文学中的「诗意」类比在电影中,也就意味着将语言学/文学和电影中的视觉、听觉和语言元素进行比较。
这种比较也许有其自身的价值,但我们必须牢记它们所代表和促成的飞跃。在这个简短的章节中,我无法对诗歌理论做一个详尽的总结,但希望能对其历史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我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文学评论家M·H·艾布拉姆斯为《普林斯顿诗歌和诗学百科全书》写的,关于此主题简洁的综述性文章。

《天堂之日》
什么是诗歌?
「诗歌」(Poetry)一词的定义在历史上发生了变化,经常引起争论。它的希腊语词根「Poiesis」的含义很广泛,不仅限于文学创作,而是指制作某物的过程,即生产行为。然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确实将这一术语应用于文学中,包括荷马史诗和古希腊剧作家的作品。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诗歌与其他艺术的区别在于它依赖文字,使用语言符号,而不是直接呈现颜色(如绘画)或身体动作(如舞蹈)。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在《诗学》以及《理想国》中认为诗歌是一种模仿的形式,是模仿的过程。作为模仿,诗歌通过文字再现了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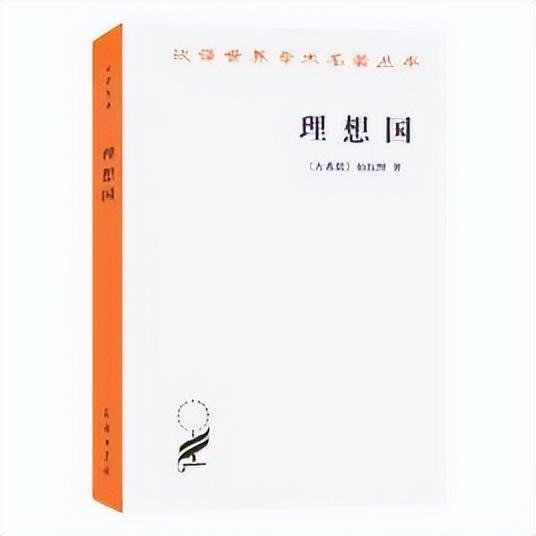
根据柏拉图的观点,模仿的过程必然涉及到与现实的距离,即思想或形式的领域。由于在柏拉图的体系中,物质世界本身是对这个神圣领域的模仿,因此世界上任何对事物的艺术模仿都只是「对模仿的模仿」,两步之遥就是真实的现实。对于柏拉图来说,诗歌使我们与现实的距离更远。
在对现实的理解中,亚里士多德排除了形式上单独的神圣领域,他并没有以同样的,对其本体论劣势的怀疑来看待模仿或诗歌。亚里士多德也没有将模仿的概念局限于对外在的盲目复制,而是声称诗歌可以(应该)寻求模仿超越现实的理想的各个方面。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诗歌不同于历史,因为它不处理真实的事件,而是虚构的事件。因此,诗歌是「一个人创造以前不存在事物的活动。」
冒着简化复杂且经常有争议的古典传统的风险,我们可以说,对于希腊人和罗马人来说,文学上的诗歌广泛地代表了虚构的行为,通过文字来创造物体、人和他们的行为的表现。但是,如果这种对诗歌的古典理解看起来很宽泛,它也很难区分。
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开始,诗歌的各种体裁被区分开来,诗歌的形式和手段,以及诗歌的修辞学开始被定义和分类。文艺复兴时期建立的新古典主义传统基于对古典概念的重新排序,定义了诗歌体裁的等级及其各自的规则,史诗和悲剧是诗歌的最高形式,抒情诗和其他形式的声望则较低。
浪漫主义时代的文学挑战了这种等级制度及其对诗歌的理解。这场革命的影响持续至今。古希腊作家、《论崇高》的作者朗吉努斯曾声称,诗歌本质上是表达情感的。十九世纪初的德国和英国浪漫主义者接受了这种说法,并使之成为现代诗歌定义的核心,将诗歌理解为诗人情感的表达。
威廉·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1798)的序言中把诗歌定义为「强大情感的自发溢出。」浪漫派颠覆了从前的桎梏,将抒情视为诗歌的本质,并将诗歌的来源——正如M·H·艾布拉姆斯所述——从对世界的模仿归为了诗人的情感。这形成了一个更为普遍的主张,即属于诗歌的感知语言系统可以和对科学指涉性、理性的语言系统形成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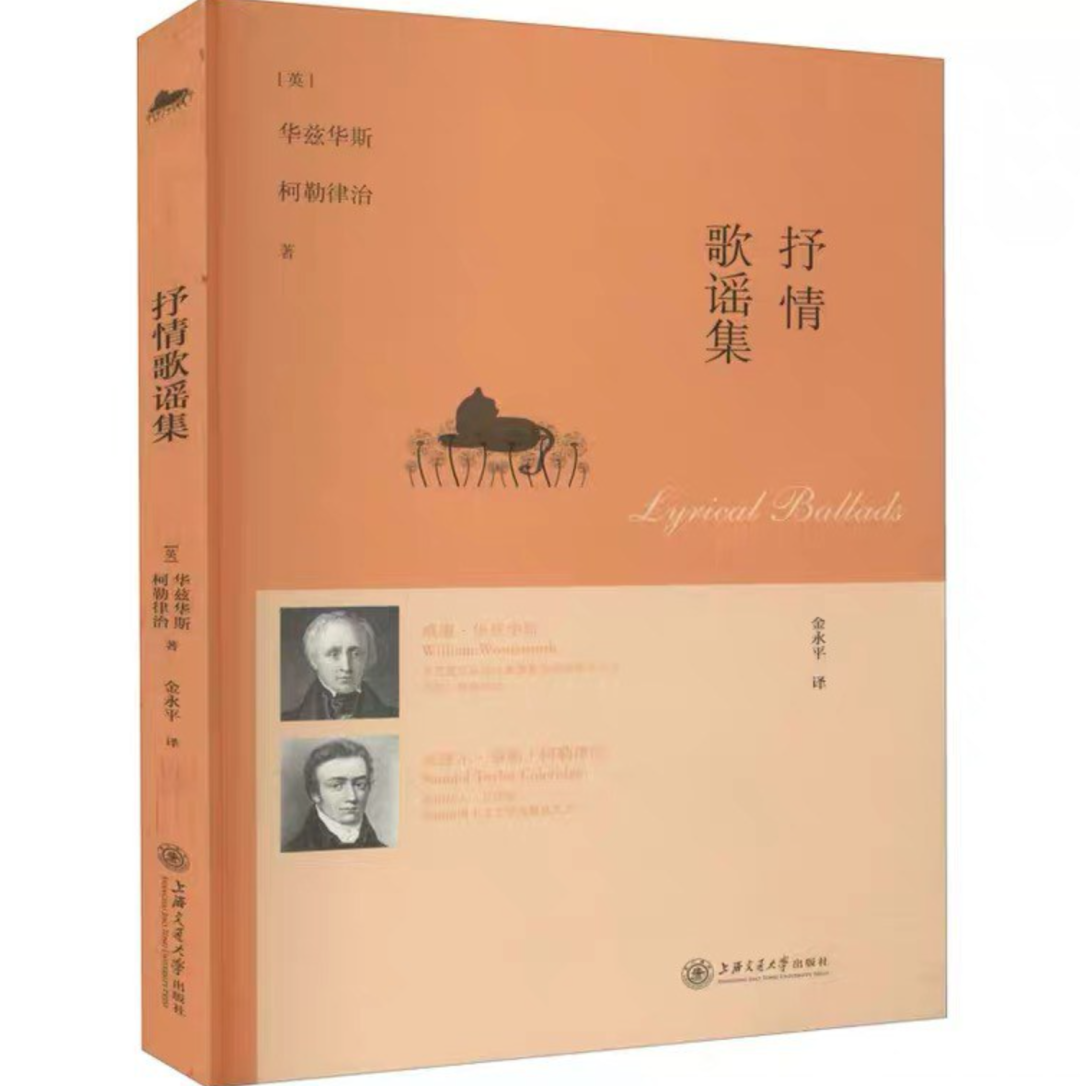
这种区别,将诗歌进一步从模仿说中剥离出来。特别是在现代主义的实践中,诗歌被定义为自给自足和自我指涉的行为,与法律、哲学或日常生活中有目的使用的语言完全对立。1788年,德国作家卡尔·菲利普·莫里茨,这位浪漫主义(事实上也是现代主义、诗歌理论)的先驱,宣称「一首诗不需要结束,它的存在和目的本身就包含了全部的价值。」
这种将诗歌视为自主性而非交流性的观点,无形中为20世纪M·H·艾布拉姆斯所谓的诗歌「客观」理论做了铺垫,并尤为关注诗歌的语言结构,以及其中的细节,用俄国形式主义者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的话来说,「一首诗是对语言的独特而具体的排布,它使语言的工具性交流的功能从属于对语言艺术性的使用。」
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与俄罗斯形式主义有关的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将诗歌具体定义为与语言的交流任务相对立的一种文学形式。正如什克洛夫斯基在他著名的文章《作为装置的艺术》中所说的那样:「诗歌的语言是成型的语言,而散文是一种普通的语言——经济、简单、适当。」对什克洛夫斯基来说,「形式」实际上意味着「去形式化」——呈现出陌生和不熟悉之感。
在这个前卫的诗歌理论中,什克洛夫斯基声称去陌生化定义了一般的艺术技巧,包括小说和短篇故事中情节或修辞的艺术性使用,以及更传统的,与传统诗歌相关的节奏和韵律的使用。基本上,这种现代主义理论延伸了卡尔·菲利普·莫里茨的主张,即诗歌本身就是一种目的。
按照形式主义者的说法,诗歌将注意力指向词语和它们的形式特征,如声音(押韵、谐音、格律、重音),而不是它们的普通含义。Zaum(超越思考)——俄国未来派的「无意义」诗歌,创造了纯粹基于声音的新词,体现了对诗歌的激进理解。
语言学家罗曼·雅克布森在年轻时与俄罗斯形式主义者(以及未来主义者)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将所谓的「诗意功能」定义为语言表述的一个方面,他将其理解为总是具有多种功能(即一种功能不需要排除其他功能)。雅克布森认为,诗意功能将注意力引向陈述本身,引向它作为一系列符号、词语的存在。
然而这并没有取消表述的交流功能,但对于语言表述来说,它主要被理解为诗意,词语——它们的声调、它们让人产生的联想——比它们的意义更重要。雅克布森承认,这种「诗意的功能」在其他情况下也会出现,但并不占主导地位。他举的最著名例子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竞选中的政治口号「我支持艾克」(I Like Ike),它传达了对候选人的支持,但其有力的效果来自韵律、押韵和其他方面的声音的诗意功能。
作为对诗歌理论大胆而先锋的补充,什克洛夫斯基的去陌生化既打开了新的视角,又引入了新的模糊性。让词语和语言变得陌生和不熟悉的过程创造了一种语言艺术,这种艺术可能超出了通常被定义为诗歌的范围。作为诗的本质的陌生化可以应用于非语言实践,如电影。
但是,诗歌是否简单地成为所有艺术实践的同义词,这是否忽视了特殊性的术语?同样,把日常语言狭隘地描述为仅仅致力于明确的交流,可能会造成一种人为的二分法。在形式主义的传统中,鲍里斯·艾肯鲍姆质疑对日常语言的这种理解,他说:「很怀疑是否真的存在一种语言,在这种语言中,我们对世界的态度将完全是一种『符号』。」
雅克布森关于诗歌功能的定义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其交流的手段上——也就是它的形式,而不是它的意义,这提供了一种对诗歌的理解——它可以在不同的媒介间跨越。
电影化的诗:改编还是影像化的阐释?
这种对文学中对「诗歌」定义的简要回顾为我们的问题提供了一些方向:什么是诗电影?虽然评论家将「诗意」一词应用于电影,但电影导演和评论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诗电影的理论。这些理论大多要么宣称诗歌由一种特定的情感表达语言组成,要么宣称将电影作为诗歌,会突出形式上的特质的形式主义理论,要么是这两种理论的结合。
我们能否将一部诗电影与作为文学现象的诗歌联系起来?诗电影是否最好直接来自于存在于文字中的诗歌?既然电影可以包括影像和文字(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那么诗电影的最好例子,是否就是其包含了一首以语言存在的诗?在电影史早期,电影的制作与诗歌有直接关系。在故事片诞生之前的时代,这种电影并不罕见。
在一战爆发前的几年里,美国著名导演格里菲斯拍摄了许多改编于具有强烈叙事内容的诗歌的电影,如《比芭走过》(Pippa Passes; or, The Song of Conscience,1909,原诗作者罗伯特·白朗宁);《迪伊之沙》(The Sands of Dee,1912,原诗作者查尔斯·金斯利;或《艾诺克·雅顿》(Enoch Arden,1911,原诗作者阿尔弗雷德·劳德·丁尼生)。

《比芭走过》
每部电影都有了引用原诗句的字幕卡,还将每首诗中对应描述的动作镜头呈现了出来。即使在一战之后,这样改编自诗歌的作品也在不断涌现,如根据C.J.丹尼斯的诗歌小说改编的澳大利亚电影《伤感的家伙》(1919),或导演弗兰克·卡普拉的第一部短片——根据吉卜林的诗歌改编的《福塔·费许的寄宿屋》(1922)。

《福塔·费许的寄宿屋》
虽然以「诗意」来描述这些电影并无问题,但它们却提出了关于这个词义的问题。这些电影都改编自叙事诗,人们可能会问,除了字幕卡中的引语,从对动作的呈现上来说,它们是否和其他叙事电影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然而,将字幕卡排除在外很难称得上是一种负责任的批判行为,这些电影中的文字和影像之间的关系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效果,与通常使用字幕卡作为解释或对话的做法截然不同。在有声时代也有电影改编诗歌的例子,如实验动画师劳伦斯·乔丹拍摄的《古舟子咏》(The Rime of Ancient Mariner,1977),在片中,奥逊·威尔斯用画外音朗读着柯勒律治的诗,背景则是古斯塔夫·多雷的动画。

《古舟子咏》
与其说这样的电影应该被认为是诗电影,不如说是电影影像对诗歌的阐释。影像为诗作插图的传统由来已久,而这些电影也许最接近这种做法。奇怪的是,法国现代主义诗人斯特凡·马拉美在他生命的晚期(也是电影史的早期)接受采访时,谈到了为诗歌作插图的做法,他有点口无遮拦地回答说,「如果你想为文学作品插图,也许电影是最有效的手段,因为它可以自动生产如此多的影像。
尽管如此,上述格里菲斯的电影通过并置影像和引用诗句的字幕卡,这两种形式达到了某种抒情的效果。《迪伊之沙》讲述了一个年轻女孩被勾引者抛弃后溺水身亡的故事,反复上演的场景以大海为背景。为了宣布女主人公的死亡,格里菲斯拍摄了海浪拍打在没有人烟的海岸上,仿佛被潮水冲刷干净。在这个镜头之前,有一个引用金斯利诗句的字幕卡。「潮水沿着海面缓缓涌来/越过海面/一圈又一圈/她却永远无法回家。」这个镜头的哀伤之美与凄美的诗句相融合,产生了超越画面的效果。

《迪伊之沙》
曼·雷的《海星》(1928)作为先锋派电影和诗电影的先声,进一步提出了影像和诗歌之间富有意味的问题。这部电影是摄影师兼导演曼·雷和诗人兼小说家罗伯特·德斯诺之间的合作,两人都曾参与超现实主义运动。尽管曼·雷表示,自己在拍摄这部电影之前就读到了德斯诺的诗,但德斯诺并没有发表这首诗,而是直接在电影中使用。

《海星》
但是,即便这首诗先于电影被创作出来,《海星》仍然与前文讨论的,那些改编自经典作品的影片有很大不同。那些电影以一种连贯的方式上演了原诗的叙事行为。相比之下,《海星》中的动作仍然显得模棱两可,难以捉摸。
影片的前三分之一部分似乎呈现了一个简单的事件:一个年轻的男人和女人相遇,他们上楼到一个房间,女人脱掉衣服躺在床上,但男人起身离开。在街上,他遇到了一个卖报纸的女人,并从她那里买了一个装在玻璃缸里的海星,他把它带到自己的房间里沉思。然而,这个动作由于通过一块有条纹的玻璃镜头被掩盖了。

《海星》
此外,字幕卡并没有解释这个动作,而是提供了反思或隐喻。在男人的思考场景后,影片不再有任何连续的动作,而是随机组合,有时围绕主题(如旅行:有火车和船的影像),或暗示仍未完成的行动(如一个女人手拿刀上楼,但没有刺伤任何人),而海星作为一个重复的意象反复出现。
我不打算解释这些意象(先锋电影史学家P·亚当斯·希特尼提供了一个精彩的解读),而是强调《海星》的画面和文字,首先以一个潜在的戏剧性来挑逗我们,然后用一系列的影像和字幕来摆脱这种期望,唤起联想而不是行动。

《海星》
海星的核心意象不断出现,字幕先后描述了玻璃、肉体和火焰的花朵,隐喻着女性和欲望的力量。开场时,男人没有和女人上床,而是盯着玻璃里的海星,这不仅是指代了弗洛伊德的恋物癖理论,也是围绕欲望的凝视,对影像和文字进行隐喻性替换。
根据叙事诗改编的电影和呈现意象而非故事的影片之间的这种对比,顺理成章地将诗电影作为主流叙事电影的替代品。这就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在何种程度上来说,电影影像可以被认为是「诗意」的?有关于诗电影的理论解决了这个问题。
文章为用户上传,仅供非商业浏览。发布者:Lomu,转转请注明出处: https://www.daogebangong.com/articles/detail/The%20highest%20state%20of%20film%20is%20poetic.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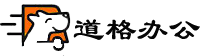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评论列表(196条)
测试